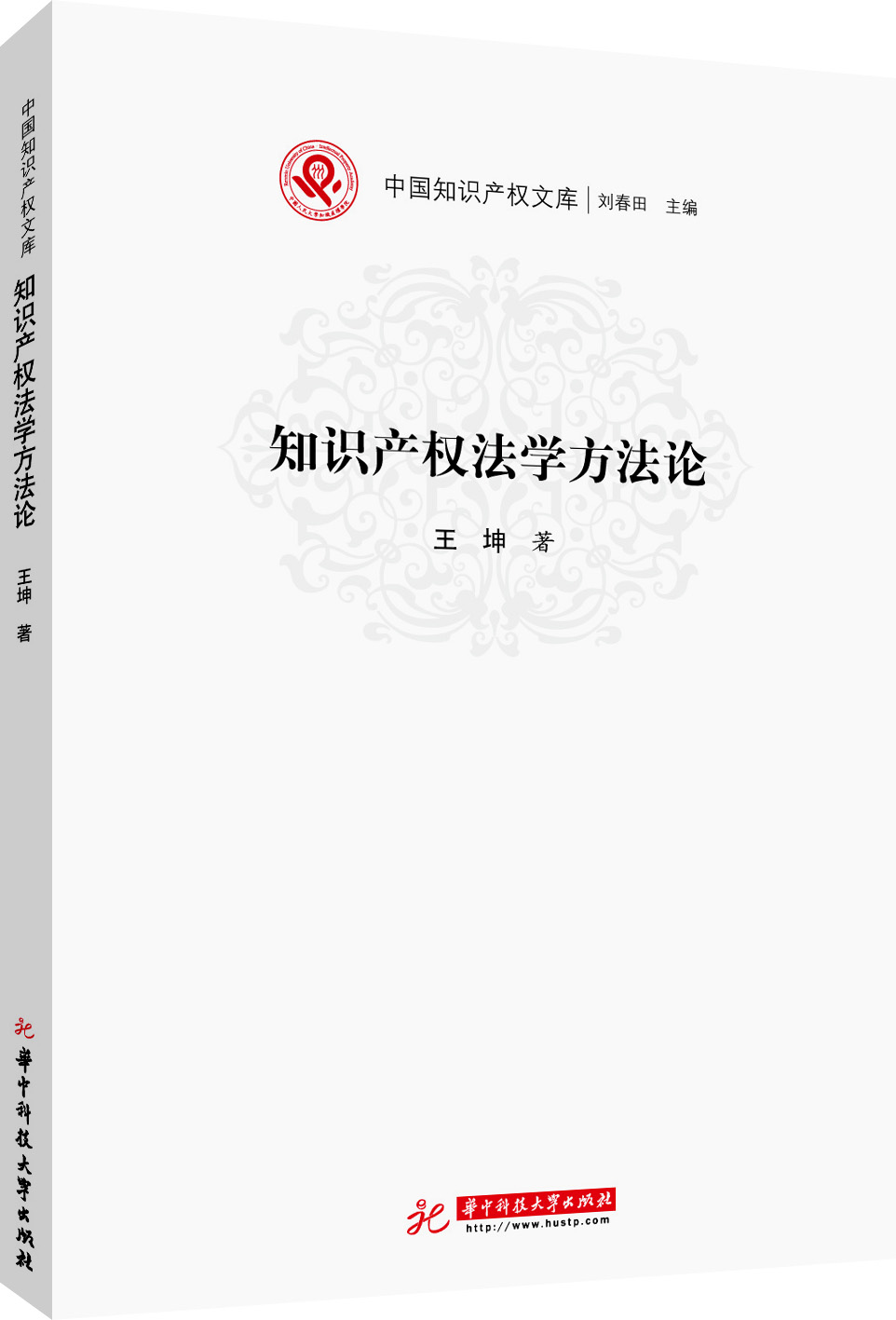《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坤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是首部关于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方面研究的专着,为《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中的一种。2016年3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基本介绍
- 书名: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
- 作者:王坤
- ISBN:978-7-5680-1376-5
- 类别:法学理论
- 定价:46.00元
-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6.03
- 装帧:平装
- 开本:1/16
内容简介
在人们心目中,智慧财产权或是智力成果权、智慧财产权、无形财产权、信息产权等概念的误称,或是着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概念的统称,本身并非科学概念,不具有法学意义。本书立论目的是:让智慧财产权成为智慧财产权,建构名实相符的智慧财产权法理论体系。基于此,本书列出智慧财产权法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各种智慧财产权共同的对象是什幺?各种智慧财产权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幺?各种智慧财产权成立和保护的一般规律是什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大解决方法。其中:知识概念分析法通过建构一个仅仅适合智慧财产权法特点和要求的知识概念,确立各种智慧财产权共同的对象,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知识功能分析法论证了各种智慧财产权之间的本质差异不在于对象的不同,而是客体的区别,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理论体系建构的关键;知识要素分析法通过分析知识要素的来源,探究不同类型智慧财产权成立和保护的一般规律,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理论体系建构的实践意义。由此,本书从建构知识概念出发,努力促使智慧财产权概念从口语到科学,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法学概念。同时,本书对智慧财产权法理论体系化路径进行大胆的深度探索,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分析各种智慧财产权问题的独特的方法体系。
作者简介
王坤,1975年生,江苏盐城人。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浙江省人民政府谘询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浙江省首期之江青年学者,兼职律师。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智慧财产权、网际网路方面的法学理论研究以及民商事法律实务工作。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着三部。
前言
提要
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存在着三种缺陷:一是上下脱节。总论部分与分论部分脱节,总论部分不能够深入到各种智慧财产权制度内部,系统地指导各部门法的研究。二是左右不通。也就是说,分论部分研究彼此之间缺少有机的关联。三是内外失调。对内,不能对智慧财产权概念进行科学定义。对外,主要是与民法之间的关係失调。总体上看,智慧财产权法学尚处于前範式阶段,没有形成协调一致、贯彻始终的理论体系。
方法是理论的出处,在理论出现问题的地方需要进行方法论上的反思。本书将智慧财产权对象设定为“知识”,智慧财产权法学有着特有的方法论,这就是知识分析方法论。具体研究路径是:首先运用符号学、信息学、系统论方面的理论成果,建构一个科学的、仅仅适合智慧财产权法特点和要求的“知识”概念,以此作为各种智慧财产权共同的对象。在此基础上,通过知识功能分析论证各种智慧财产权之间的本质区别,通过知识要素分析研究智慧财产权成立和保护的一般规律,使得智慧财产权真正地成为智慧财产权。由此,知识概念分析、知识功能分析以及知识要素分析共同构成知识分析方法,并成为智慧财产权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理论架构,本书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导论主要包括三节: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的意义,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智慧财产权法学是一种病态的学科,没有值得一提的理论体系,因而需要从方法论层面上进行反思;第二节主要是论述了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概念界定和地位,认为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属于智慧财产权法哲学的组成部分。不过,本书所指的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是一种狭义的方法论,特指知识分析方法论;第三节主要是论述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和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之间的关係,认为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是实现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的具体路径。
第一章是知识概念分析法。首先通过符号学、信息学、系统论建构科学的知识概念,认为在智慧财产权法上,知识是一种符号组合,包括符号形式和符号信息两个层次。接着,认为智慧财产权法上的知识应当具有创新性和系统性,这两个特徵使得知识具有可支配性、商业价值性,从而能够成为智慧财产权的对象。本章的最后部分集中论述了知识概念的科学建构对于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第二章是知识功能分析法。首先论述知识功能分析的概念,再分别研究作品功能、商标功能、专利功能与相应的智慧财产权权能体系之间的关係,论证知识功能是智慧财产权权能体系建构的核心和灵魂。本章的最后部分集中论述了知识功能分析对于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第三章是知识要素分析法。本章首先论述各种知识,包括作品、商标和专利都不是混沌直观的整体,而是由符号形式和符号信息两个层次上的各种要素构成。根据来源的不同,这些要素可以区分为存量要素和增量要素两种。接着简要描述了知识要素的分类,探讨知识要素分析的正当性基础,研究知识要素分析法在智慧财产权法上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套用情况,最后集中论述知识要素分析对于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从经验到理论——刘春田教授《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总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终于问世。《文库》力图反映中国人在智慧财产权问题上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汇集中国智慧财产权的经验总结、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重要文献,为逐步构建中国的智慧财产权法律理论与科学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文库》也为中国,乃至世界法律文化的积澱,注入丰富的内涵。
智慧财产权制度起源于西方创立的工业文明。几百年来,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它功能利弊的褒贬,从其出现伊始,就争议不断。今天,人类已进入新经济时代。无论已开发国家,还是开发中国家,都普遍採用了数位技术。当前,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智慧财产权保护,已成为人类进步的基本手段。历史证明,智慧财产权制度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複杂的社会现象,它藉助于机构、制度的力量,已成为将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为一体的系统机制,对它的技术、文化、经济和法律理论分析、历史探究,乃至哲学思考,一再吸引着科学、技术、经济和法律学人的目光。在中国,自晚清起,百余年来,也引起矢志复兴民族,力图融入现代文明的志士仁人对其本质的追问与思考,和对其社会功能的得失权衡。中国的智慧财产权制度是世界智慧财产权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智慧财产权的理论,是以国门开启和不断改革开放、渐进融入世界为背景,在传统与现代接续,西学与国情结合的条件下,以中国乃至世界智慧财产权的表达与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产物。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受论者心胸狭隘和眼界偏执的局限,对从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遑论研究,基本没有概念。更无脉络可循,没有资格作任何评断。这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一课。否则,数典忘祖,没有资格谈论今天。本文暂且略去既往的历史,以新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我以为,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30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主要是制度诠释和转入理论建设的两个阶段,其中,前15年大体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还处于初期。
第一阶段:理论空白与经验贫瘠背景下的制度诠释。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为中国重建智慧财产权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随后,智慧财产权法制建设和研究同步开展。在漫长的智慧财产权诸法律的初创阶段,中国的法学家集中其学识与智慧,一边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制度,包括法律文本的研究和实地考察,一边比照变动不居的国情,从智慧财产权法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体系设计、制度安排、对外关係等基础问题,乃至于具体规範的推敲、条文的表述,作出儘可能合理的表述,为我国智慧财产权法律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种贡献难能可贵。但是,由于智慧财产权理论的空白,又缺乏民法精神、理论与制度的涵养,既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可以依循,也没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可供总结。国门初开,计画经济时代的学者,面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法律制度,囿于学识与眼界,既陌生,又新奇。既无足够的条件深刻理解西方已历时数百年的成熟制度,也难以把握举棋不定、变革中的中国社会走向。早期的智慧财产权研究,在无理论基础、无历史传统、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既不能对智慧财产权一般问题进行思考,也难以对具体制度深入研究。所有资讯,鹹自西方舶来。所谓研究,不啻学步。主要是按照西方的思维,对国际条约和外国法律制度进行文本介绍,以及对墨迹未乾的中国法律档案的粗浅说明。智慧财产权法的出版物,基本上以各种各样的“解说”、“概论”为主,照猫画虎,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严格地讲,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不清楚什幺是理论。在学理上,智慧财产权法既无逻辑起点,又找不到理论归宿,就像离群索居的孤雁,几成法学理论的孤儿。
第二阶段,从制度诠释到理论建设。首先要正视一个事实:中国人不是超人。在智慧财产权法制建设上,西方二百年的路,中国人并非二十年走过,而是断断续续地走了一百年。遗憾的是,正是这中断的几十年,造成了理论上的真空。因此,无论制度构造,还是理论建设,鹹自基本概念开始,从头做起,扎扎实实,一步一跬,才是唯一的出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智慧财产权法律构架的完成,尤其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逐渐转变,对外交流的繁荣,利益冲突与法律纠纷的频仍,导致实践的召唤和理论供给短缺这一矛盾日趋尖锐。恰是这一矛盾,成了一个突破口,把智慧财产权研究推进了新的阶段。这阶段的研究逐渐突破了旧有模式的藩篱,摆脱亦步亦趋、鹦鹉学舌的窘境;开始探讨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智慧财产权法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智慧财产权的高等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已毕业的40多位攻读智慧财产权法学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半数以上的论文选题或出站报告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他们分别对智慧财产权的基本概念、法律属性、对象与客体、法律体系建构、价值评估、侵权赔偿、归责原则、专门制度、历史梳理、文化价值乃至哲学基础等智慧财产权和与智慧财产权最密切联繫的基本範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等诸多的学术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博士论文选择基础问题研究。其他学者,也有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智慧财产权的纵深,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一时期,和相对粗陋的制度诠释相比,青出于蓝,胜于蓝,是一个质的飞跃。智慧财产权的研究进入了理论建设的阶段。今天,经过15年左右的积累,智慧财产权的研究,百花齐放,蔚然成风。这种局面,为《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的萌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应当不断进步,从经验走向理论,从感性走向理性,走向科学。目前的研究,大体呈现两条路径:一条主要表现为对理论和制度表达的研究与参悟。面对外部世界,中国人有如婴儿吮吸母乳,贪婪地学习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这类主要是文本研究,多出于博士论文。另一条则偏重司法实践中对概念的诠释和具体制度的运用。面对司法实践,深入生活,尽其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力求为社会纠纷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基本属于经验总结,主要表现为法官的办案体验。这两类成果,都有相当的建树。所缺者,是从经验到理论,能将两条路径连线起来,形成从实践到经验,再从经验升华为理论,又服务于实践的逻辑链条的成果。这是更接近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知识。智慧财产权理论,源自社会实践,源自对实践的经验总结。经验是可贵的,在强调经验时,论者常以霍姆斯的观点为据: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又:“历史研究之一页当抵逻辑分析之一卷”(转引自:黄海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智慧财产权的表达与实践:着作权、专利与商标的历史考察》第1页)。但是,简单比较经验与知识的优劣是片面的。“体验和知识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德]M石里克:《普通认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0页)“谁要是接近事物,参与事物活动的方法和运作,他就是在从事生命活动而不是从事认知活动;对他来说,事物展示的是其价值方面,而不是其本质”(同前书,第106-107页)。经验还只是感性认识,只是走向理性认识的一个阶段。“经验使我们得以融入事物或事物得以融进我们之中的直观,但它仍然不构成知识。我们不能通过直观来理解或解释任何东西。通过直观的方式我们能获得的只是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对事物的理解。而只有对事物的理解才是我们在科学和哲学中追求知识所要达到的目标”(同前书,第110页)。经验唯有纳入科学思维的体系,才能上升为理性。中西传统,各有所长。与霍姆斯同时代的晚清大儒沈家本持论更显全面、公允,他认为:“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不明学理,则经验者无以会其通;不习经验,则学理亦无从证其是。经验与学理,正两相需也”(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四集,2217页)。可见,经验和理论,二者更像“术”和“道”,是辩证的关係,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不分伯仲。两厢不宜做价值比较和优劣评断。
在源归民法理论本土的基础上,对智慧财产权而言,更为重要的研究,或称核心问题,是“寻找自己”。所谓“自己”:
(一)在保持私法基因的前提下,划清与物权法、债权法、人格权法的界限,进入智慧财产权的自我世界、独有空间,寻找一个特殊的自身。智慧财产权作为绝对权利,和人格权、物权有相通之处;作为财产权利,则与物权“似曾相识”,均属于“对世权”等,但毕竟“知识”不是“物”,对智慧财产权的研究应当围绕着“知识”进行。参照物权理论对智慧财产权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智慧财产权并非“準物权”。以物权类比智慧财产权,用“準物权”的思维去套用“智慧财产权”是否可取,值得商榷。人类既可基于对“知识”的支配带来利益,也可基于对“物”的支配带来利益。但是产生利益的途径,无论範围、方式、手段,都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另类的财产形态,论者应当考虑再辟蹊径,寻找智慧财产权自身的本质与规律。
(二)回到原点,全方位认识智慧财产权。知识创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导。“智慧财产权是资本主义核心规範的一部分”([美]苏珊·K塞尔着:《私权、公法——智慧财产权的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24页)私权是智慧财产权法律性质的基石,但它只是问题的一个剖面。“知识”在其创造、保存、扩散、管理、经营过程中,会发生比其他传统财产权複杂得多的社会关係,这些关係是如何发生、变动和消灭的,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智慧财产权制度是如何构建,又是如何实践的,都值得深入研究。“资本家的企业需要国家为其聚集提供政治和社会条件”(同前书,第41页)。已开发国家几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围绕智慧财产权问题所建立的体系、机构、制度,远比中国人有限的体验和由此激发的想像要複杂得多。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以积极的精神,从容、淡定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要全方位地认识智慧财产权,必须回到原点,从头做起。这是智慧财产权学者的长期任务。
(三)在坚实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智慧财产权法的理论体系。用逐渐丰富的理论的营养,反哺与时俱进的制度。与此相对应,还需建立一套理性、科学的智慧财产权法的知识体系。因此,当代智慧财产权学人将面临无法穷尽的挑战和永不完结的任务。这正是智慧财产权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不竭的资源所在。
(四)釐清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关係,从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找到自我。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人类世界存在着普世价值。这是大家可以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理由。当今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任何一种独特生活方式,都不是单一的,都是多种元素的组合。每种元素,都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国家、种族。所谓独特,不过是特定的组合。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準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527页)。我们还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还有基于传统、现实、交流和全球化背景而形成的各自生活方式。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找到特殊之处,找到它特殊的质、特殊的生成及其运动规律。
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总体上讲,恰似少年。正因为年轻,才蛰伏着无穷的潜力,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希望。希望《文库》,以及一切有益的成果,成为中国智慧财产权理论建设的历史写照。
《文库》欢迎优秀的智慧财产权学术成果加盟,同时也吁请学界同仁,尽其所能,整理优秀的历史成果,再现给学界与社会。相信,从历史中走过的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必有辉煌的未来。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感谢他们的眼界、识见、大度和包容。众所周知,科学研究不图回报,是学者推崇的风範。但是,对出版者而言,营利是它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企业道德。当代,不计回报,倾力扶助学术的出版社,已不多见。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身上,我看到了张元济辈中国传统出版家的影子。法律分社王京图社长对待《文库》,彰显了出版家的情怀。他心态平和,目光悠远,看到的不是眼前的数字码洋、营利业绩,而是学术的未来。与他合作,十分愉快。
刘春田
2010年9月28日于人大明德楼
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存在着三种缺陷:一是上下脱节。总论部分与分论部分脱节,总论部分不能够深入到各种智慧财产权制度内部,系统地指导各部门法的研究。二是左右不通。也就是说,分论部分研究彼此之间缺少有机的关联。三是内外失调。对内,不能对智慧财产权概念进行科学定义。对外,主要是与民法之间的关係失调。总体上看,智慧财产权法学尚处于前範式阶段,没有形成协调一致、贯彻始终的理论体系。
方法是理论的出处,在理论出现问题的地方需要进行方法论上的反思。本书将智慧财产权对象设定为“知识”,智慧财产权法学有着特有的方法论,这就是知识分析方法论。具体研究路径是:首先运用符号学、信息学、系统论方面的理论成果,建构一个科学的、仅仅适合智慧财产权法特点和要求的“知识”概念,以此作为各种智慧财产权共同的对象。在此基础上,通过知识功能分析论证各种智慧财产权之间的本质区别,通过知识要素分析研究智慧财产权成立和保护的一般规律,使得智慧财产权真正地成为智慧财产权。由此,知识概念分析、知识功能分析以及知识要素分析共同构成知识分析方法,并成为智慧财产权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理论架构,本书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导论主要包括三节: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的意义,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智慧财产权法学是一种病态的学科,没有值得一提的理论体系,因而需要从方法论层面上进行反思;第二节主要是论述了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概念界定和地位,认为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属于智慧财产权法哲学的组成部分。不过,本书所指的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是一种狭义的方法论,特指知识分析方法论;第三节主要是论述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和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之间的关係,认为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是实现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的具体路径。
第一章是知识概念分析法。首先通过符号学、信息学、系统论建构科学的知识概念,认为在智慧财产权法上,知识是一种符号组合,包括符号形式和符号信息两个层次。接着,认为智慧财产权法上的知识应当具有创新性和系统性,这两个特徵使得知识具有可支配性、商业价值性,从而能够成为智慧财产权的对象。本章的最后部分集中论述了知识概念的科学建构对于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第二章是知识功能分析法。首先论述知识功能分析的概念,再分别研究作品功能、商标功能、专利功能与相应的智慧财产权权能体系之间的关係,论证知识功能是智慧财产权权能体系建构的核心和灵魂。本章的最后部分集中论述了知识功能分析对于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第三章是知识要素分析法。本章首先论述各种知识,包括作品、商标和专利都不是混沌直观的整体,而是由符号形式和符号信息两个层次上的各种要素构成。根据来源的不同,这些要素可以区分为存量要素和增量要素两种。接着简要描述了知识要素的分类,探讨知识要素分析的正当性基础,研究知识要素分析法在智慧财产权法上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套用情况,最后集中论述知识要素分析对于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从经验到理论——刘春田教授《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总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终于问世。《文库》力图反映中国人在智慧财产权问题上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汇集中国智慧财产权的经验总结、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重要文献,为逐步构建中国的智慧财产权法律理论与科学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文库》也为中国,乃至世界法律文化的积澱,注入丰富的内涵。
智慧财产权制度起源于西方创立的工业文明。几百年来,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它功能利弊的褒贬,从其出现伊始,就争议不断。今天,人类已进入新经济时代。无论已开发国家,还是开发中国家,都普遍採用了数位技术。当前,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智慧财产权保护,已成为人类进步的基本手段。历史证明,智慧财产权制度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複杂的社会现象,它藉助于机构、制度的力量,已成为将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为一体的系统机制,对它的技术、文化、经济和法律理论分析、历史探究,乃至哲学思考,一再吸引着科学、技术、经济和法律学人的目光。在中国,自晚清起,百余年来,也引起矢志复兴民族,力图融入现代文明的志士仁人对其本质的追问与思考,和对其社会功能的得失权衡。中国的智慧财产权制度是世界智慧财产权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智慧财产权的理论,是以国门开启和不断改革开放、渐进融入世界为背景,在传统与现代接续,西学与国情结合的条件下,以中国乃至世界智慧财产权的表达与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产物。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受论者心胸狭隘和眼界偏执的局限,对从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遑论研究,基本没有概念。更无脉络可循,没有资格作任何评断。这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一课。否则,数典忘祖,没有资格谈论今天。本文暂且略去既往的历史,以新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我以为,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30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主要是制度诠释和转入理论建设的两个阶段,其中,前15年大体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还处于初期。
第一阶段:理论空白与经验贫瘠背景下的制度诠释。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为中国重建智慧财产权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随后,智慧财产权法制建设和研究同步开展。在漫长的智慧财产权诸法律的初创阶段,中国的法学家集中其学识与智慧,一边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制度,包括法律文本的研究和实地考察,一边比照变动不居的国情,从智慧财产权法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体系设计、制度安排、对外关係等基础问题,乃至于具体规範的推敲、条文的表述,作出儘可能合理的表述,为我国智慧财产权法律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种贡献难能可贵。但是,由于智慧财产权理论的空白,又缺乏民法精神、理论与制度的涵养,既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可以依循,也没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可供总结。国门初开,计画经济时代的学者,面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法律制度,囿于学识与眼界,既陌生,又新奇。既无足够的条件深刻理解西方已历时数百年的成熟制度,也难以把握举棋不定、变革中的中国社会走向。早期的智慧财产权研究,在无理论基础、无历史传统、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既不能对智慧财产权一般问题进行思考,也难以对具体制度深入研究。所有资讯,鹹自西方舶来。所谓研究,不啻学步。主要是按照西方的思维,对国际条约和外国法律制度进行文本介绍,以及对墨迹未乾的中国法律档案的粗浅说明。智慧财产权法的出版物,基本上以各种各样的“解说”、“概论”为主,照猫画虎,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严格地讲,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不清楚什幺是理论。在学理上,智慧财产权法既无逻辑起点,又找不到理论归宿,就像离群索居的孤雁,几成法学理论的孤儿。
第二阶段,从制度诠释到理论建设。首先要正视一个事实:中国人不是超人。在智慧财产权法制建设上,西方二百年的路,中国人并非二十年走过,而是断断续续地走了一百年。遗憾的是,正是这中断的几十年,造成了理论上的真空。因此,无论制度构造,还是理论建设,鹹自基本概念开始,从头做起,扎扎实实,一步一跬,才是唯一的出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智慧财产权法律构架的完成,尤其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逐渐转变,对外交流的繁荣,利益冲突与法律纠纷的频仍,导致实践的召唤和理论供给短缺这一矛盾日趋尖锐。恰是这一矛盾,成了一个突破口,把智慧财产权研究推进了新的阶段。这阶段的研究逐渐突破了旧有模式的藩篱,摆脱亦步亦趋、鹦鹉学舌的窘境;开始探讨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智慧财产权法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智慧财产权的高等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已毕业的40多位攻读智慧财产权法学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半数以上的论文选题或出站报告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他们分别对智慧财产权的基本概念、法律属性、对象与客体、法律体系建构、价值评估、侵权赔偿、归责原则、专门制度、历史梳理、文化价值乃至哲学基础等智慧财产权和与智慧财产权最密切联繫的基本範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等诸多的学术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博士论文选择基础问题研究。其他学者,也有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智慧财产权的纵深,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一时期,和相对粗陋的制度诠释相比,青出于蓝,胜于蓝,是一个质的飞跃。智慧财产权的研究进入了理论建设的阶段。今天,经过15年左右的积累,智慧财产权的研究,百花齐放,蔚然成风。这种局面,为《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的萌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应当不断进步,从经验走向理论,从感性走向理性,走向科学。目前的研究,大体呈现两条路径:一条主要表现为对理论和制度表达的研究与参悟。面对外部世界,中国人有如婴儿吮吸母乳,贪婪地学习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这类主要是文本研究,多出于博士论文。另一条则偏重司法实践中对概念的诠释和具体制度的运用。面对司法实践,深入生活,尽其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力求为社会纠纷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基本属于经验总结,主要表现为法官的办案体验。这两类成果,都有相当的建树。所缺者,是从经验到理论,能将两条路径连线起来,形成从实践到经验,再从经验升华为理论,又服务于实践的逻辑链条的成果。这是更接近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知识。智慧财产权理论,源自社会实践,源自对实践的经验总结。经验是可贵的,在强调经验时,论者常以霍姆斯的观点为据: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又:“历史研究之一页当抵逻辑分析之一卷”(转引自:黄海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智慧财产权的表达与实践:着作权、专利与商标的历史考察》第1页)。但是,简单比较经验与知识的优劣是片面的。“体验和知识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德]M石里克:《普通认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0页)“谁要是接近事物,参与事物活动的方法和运作,他就是在从事生命活动而不是从事认知活动;对他来说,事物展示的是其价值方面,而不是其本质”(同前书,第106-107页)。经验还只是感性认识,只是走向理性认识的一个阶段。“经验使我们得以融入事物或事物得以融进我们之中的直观,但它仍然不构成知识。我们不能通过直观来理解或解释任何东西。通过直观的方式我们能获得的只是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对事物的理解。而只有对事物的理解才是我们在科学和哲学中追求知识所要达到的目标”(同前书,第110页)。经验唯有纳入科学思维的体系,才能上升为理性。中西传统,各有所长。与霍姆斯同时代的晚清大儒沈家本持论更显全面、公允,他认为:“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不明学理,则经验者无以会其通;不习经验,则学理亦无从证其是。经验与学理,正两相需也”(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四集,2217页)。可见,经验和理论,二者更像“术”和“道”,是辩证的关係,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不分伯仲。两厢不宜做价值比较和优劣评断。
在源归民法理论本土的基础上,对智慧财产权而言,更为重要的研究,或称核心问题,是“寻找自己”。所谓“自己”:
(一)在保持私法基因的前提下,划清与物权法、债权法、人格权法的界限,进入智慧财产权的自我世界、独有空间,寻找一个特殊的自身。智慧财产权作为绝对权利,和人格权、物权有相通之处;作为财产权利,则与物权“似曾相识”,均属于“对世权”等,但毕竟“知识”不是“物”,对智慧财产权的研究应当围绕着“知识”进行。参照物权理论对智慧财产权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智慧财产权并非“準物权”。以物权类比智慧财产权,用“準物权”的思维去套用“智慧财产权”是否可取,值得商榷。人类既可基于对“知识”的支配带来利益,也可基于对“物”的支配带来利益。但是产生利益的途径,无论範围、方式、手段,都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另类的财产形态,论者应当考虑再辟蹊径,寻找智慧财产权自身的本质与规律。
(二)回到原点,全方位认识智慧财产权。知识创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导。“智慧财产权是资本主义核心规範的一部分”([美]苏珊·K塞尔着:《私权、公法——智慧财产权的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24页)私权是智慧财产权法律性质的基石,但它只是问题的一个剖面。“知识”在其创造、保存、扩散、管理、经营过程中,会发生比其他传统财产权複杂得多的社会关係,这些关係是如何发生、变动和消灭的,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智慧财产权制度是如何构建,又是如何实践的,都值得深入研究。“资本家的企业需要国家为其聚集提供政治和社会条件”(同前书,第41页)。已开发国家几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围绕智慧财产权问题所建立的体系、机构、制度,远比中国人有限的体验和由此激发的想像要複杂得多。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以积极的精神,从容、淡定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要全方位地认识智慧财产权,必须回到原点,从头做起。这是智慧财产权学者的长期任务。
(三)在坚实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智慧财产权法的理论体系。用逐渐丰富的理论的营养,反哺与时俱进的制度。与此相对应,还需建立一套理性、科学的智慧财产权法的知识体系。因此,当代智慧财产权学人将面临无法穷尽的挑战和永不完结的任务。这正是智慧财产权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智慧财产权文库》不竭的资源所在。
(四)釐清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关係,从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找到自我。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人类世界存在着普世价值。这是大家可以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理由。当今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任何一种独特生活方式,都不是单一的,都是多种元素的组合。每种元素,都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国家、种族。所谓独特,不过是特定的组合。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準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527页)。我们还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还有基于传统、现实、交流和全球化背景而形成的各自生活方式。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找到特殊之处,找到它特殊的质、特殊的生成及其运动规律。
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总体上讲,恰似少年。正因为年轻,才蛰伏着无穷的潜力,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希望。希望《文库》,以及一切有益的成果,成为中国智慧财产权理论建设的历史写照。
《文库》欢迎优秀的智慧财产权学术成果加盟,同时也吁请学界同仁,尽其所能,整理优秀的历史成果,再现给学界与社会。相信,从历史中走过的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研究,必有辉煌的未来。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感谢他们的眼界、识见、大度和包容。众所周知,科学研究不图回报,是学者推崇的风範。但是,对出版者而言,营利是它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企业道德。当代,不计回报,倾力扶助学术的出版社,已不多见。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身上,我看到了张元济辈中国传统出版家的影子。法律分社王京图社长对待《文库》,彰显了出版家的情怀。他心态平和,目光悠远,看到的不是眼前的数字码洋、营利业绩,而是学术的未来。与他合作,十分愉快。
刘春田
2010年9月28日于人大明德楼
目录
导论 为什幺是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
第一节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一、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现状
二、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节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概念与研究对象
二、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的法律地位
三、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渊源
第三节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与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
一、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的分歧
二、“不构派”述评
三、“建构派”述评
四、方法论研究对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面临的三个重大问题的解决
第一章知识概念分析法
第一节知识概念分析法概述
一、建构科学的概念体系的必要性
二、现行智慧财产权法学概念体系存在的缺陷
三、“知识”概念的科学建构
第二节知识概念的要素之一——符号
一、符号概念
二、符号分类及其对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三、符号特点及其对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第三节知识概念的要素之二——信息
一、信息概念
二、信息和符号之间的关係
第四节知识概念的要素之三——系统性、创新性
一、系统性
二、创新性
第五节知识概念分析对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一、有助于初步建构作品、商标、专利等概念
二、有助于确定智慧财产权概念
三、有助于界定着作权(智慧财产权)与传播者权(邻接权)之间的关係
四、有助于确定表演者权的性质
五、有助于实现智慧财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
六、有助于研究智慧财产权的特徵
七、小结
第二章知识功能分析法
第一节知识功能分析概述
一、功能概述
二、知识功能
第二节作品功能与着作权权能体系
一、作品的精神功能
二、作品功能与着作权权能体系的建构
第三节商标功能与商标权权能体系
一、商标的实用销售功能
二、商标功能与商标权权能体系的建构
第四节专利功能与专利权权能体系
一、专利的实用技术功能
二、专利权权能体系
三、禁止平行进口能否成为专利权的权能
第五节知识功能分析对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一、有助于作品、商标、专利等概念的深度建构
二、有助于区分智慧财产权对象和客体,明晰各种智慧财产权之间的本质区别
三、有助于判断智慧财产权能否成立
四、有助于判断智慧财产权保护的範围
五、有助于解释智慧财产权法上的一些疑难问题
六、小结
第三章知识要素分析法
第一节知识要素分析概述
一、知识要素分析的可能性
二、知识要素的实证分析
三、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知识要素分类
一、存量要素的分类
二、增量要素的分类
第三节知识要素分析法的正当性
一、基于劳动说的分析
二、基于激励说的分析
三、基于社会规划说的分析
四、基于人格说的分析
五、小结
第四节知识要素分析法的渊源
一、学界对知识要素分析法的论述
二、知识要素分析法在实务中的套用
第五节知识要素分析对智慧财产权法的意义
一、衡量是否授予智慧财产权
二、确定智慧财产权保护範围
三、分析智慧财产权对象相互之间的关係
四、小结
结语 为智慧财产权法体系化而奋斗
参考文献
基础文献
后记
精彩文摘
导论 为什幺是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
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是不是妖怪,但搞不清楚是何方妖怪,仅凭自身的力量很难除之。如来佛更为厉害,能够算出妖怪的出处,因而降妖除魔的法力更为强大。在社会科学中,方法就是理论的出处,理论上的辩驳往往也需要上升到方法的层面上。一旦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上,很多“假理论”就如妖孽一样现出了原形。
第一节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一、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现状
在智慧财产权法研究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奇特的画面:
首先,上下脱节。在总论部分,有着众多观点分歧,智力成果权说、无形财产权说、信息产权说、符号产权说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观点往往高高在上,与分论部分脱节,不能够深入到各种智慧财产权制度内部,系统地指导各部门法的研究。
其次,左右不通。也就是说,分论部分研究彼此之间缺少有机的关联。比如,商标显着性、作品独创性、专利新颖性彼此之间有无关联?商标和作品、专利之间是什幺关係?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繫和区别是什幺?很少有人去进行专门的研究,分论部分之间常常呈现出一幅分疆裂土、各守领地、互不往来的景象。
最后,内外失调。对内,智慧财产权概念的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以至于只能用列举的方式对智慧财产权概念进行定义。对外,主要是与民法之间的关係失调。各种智慧财产权问题,比如外观设计、实用艺术品等智慧财产权对象是否受到多重保护?真的存在着所谓着作人格权吗?着作权人具有複製权、发行权、改编权等多种着作权财产权吗?如何解释智慧财产权权利穷竭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常常不符合民法的逻辑,往往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就此展开的各种观点基本上是在经验层面上各执一端,自说自话,莫衷一是,以至于智慧财产权法长期游离于民法体系之外。
整个智慧财产权法研究状况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王纲解纽,只存在着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如同智慧财产权总论部分之虚弱。而诸侯并起,纷争不已,又肖似智慧财产权分论中之争议。无论是身处智慧财产权法学界之内,还是置身其外,都能切实地感受到一个“乱”字。
为什幺会出现这种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何为理论以及如何建构智慧财产权理论。“倘法学能称之为科学,端在理论。”
引自刘春田教授给杨雄文所着《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智慧财产权》一书所撰写的序言,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从形式上看,理论是由基本概念、原理及各种推论构成的知识体系。库恩提出衡量理论优劣的5个标準: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理论应当符合下面几个标準:
(1)精确性。作为一个理论,或是需要来自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撑,或是需要翔实的经验实验材料的支持,或是二者兼备。比如,费孝通先生在对经验现象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提炼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差序格局等,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
(2)一致性。理论是用概念之网赋予世界以秩序,必须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而法学的生命一定是逻辑,而不是经验。法学中不能容忍经验层面上的观点纷争,必须形成一个内在协调一致的体系。
(3)广泛性。理论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应当儘可能地涵盖更多的现象。而理论越是抽象和巨观,就越能从整体上观察、思考研究对象的总体规律,越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牛顿正是凭藉着“神一般的思维力”,把巨观物体的机械运动都统一于万有引力。可以说,如果不脱离常识,不超越经验,就难以形成真正的理论。
(4)简单性。科学基础的逻辑简单性是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甚至可以说,简单往往是深刻的代名词。简单还是对理论进行审美的要求,“评价一个理论美不美,标準正是原理上的简单性,而不是技术上的困难性”
而要达致简单性,需要以儘可能少的前提条件作为建构理论的起点。比如,个体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等四个基本假设基础上,
在这些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推导出系统的理论。再如,爱因斯坦认为,物理科学的基础乃是“由最少数的概念和基本关係所组成,从它那里,可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各个分科的一切概念和一切关係”
(5)有效性。也就是说,理论经由一系列的中介,能够有效地进行演绎,由此形成的具体结论和命题能够切合实际,在自然科学中能够被实验所证实或证伪,在社会科学中能够产生具体的社会效果,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从理论自身存在状态上看,一定要具有广泛性,要脱离常识,超越经验,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理论。但从理论的效用上看,则需要能够联繫现实,指导实践,产生效果。
如果我们把理论比作一个人的话,精确性如同腿脚健壮、稳如磐石;一致性如同经脉畅通、气血调和;广泛性如同思维深邃、神目如电;简单性如同胖瘦适中、骨骼清奇;有效性则如同猿臂轻舒、十指灵巧。一个好的理论犹如古希腊着名雕塑家米隆所创作的“掷铁饼者”形象,给人以生命力爆发的震撼以及无尽的艺术享受。
掷铁饼者
用以上五个标準进行判断,我们会发现在目前智慧财产权法学总论部分,多数学说具备了广泛性、一致性、简单性三个特徵,但在精确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则参差不齐。有的观点,比如智力成果权说、无形财产权说等学说诉诸人的感官,既缺少强有力的支撑理论,也没有得到经验材料的支持,在精确性方面存在问题。另外,更为致命的是,绝大部分观点对于分则部分的研究并无多大的帮助,不能对商标显着性、作品独创性等核心概念作出富有意义的说明。这些观点本身既无法证实,也无从证伪,不能始终如一地去指导分论部分的研究,根本就缺少有效性。直接导致总论部分沦为空洞的议论,常常同智慧财产权实践分离,飘在半空下不来;而分论部分则流于经验的描述,往往与民法理论绝缘,趴在地上起不来。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儘管大部分智慧财产权教科书的总论言之凿凿,立论皇皇,一日弃之,除了使得教科书不至过于厚重以外,基本不会影响分论的学习。可以说,总论部分的玄学性与分论部分的经验性,构成诸多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缺陷。
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状况与我国古代科技极为类似。以医学为例,根据许倬云先生的看法,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把人的整个身体当作一个系统。但是从《本草纲目》和《伤寒论》两本书来看,中国医学可以脱离形上学的理论,而从实证上抽取经验,记录药物性质及病的现象。所以,中国医学实际上是两套东西来相配的,理论常常不过是点缀,医学的套用则是靠实际的检验所得出来的结果。农学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科学和技术是脱节的,科学沦为玄学,技术则流于经验,这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其名着《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经提出科学进步的三个阶段:一是前範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存在着各种理论派别,彼此纷争,莫衷一是;二是範式确立阶段。这个阶段中确立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方法、基本命题;三是危机阶段。旧的範式趋于崩溃,有待于建立新範式。库恩认为:“取得了一个範式,取得了範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誌。”
但是,智慧财产权法目前所处的阶段远没有达到前範式阶段。其中的原因在于:还没有哪一种观点能够演化为系统的理论,既能够统合自身,又能够指导实践。也就是说,在智慧财产权法学界,还没有从春秋诸侯纷争过渡到战国七雄争霸,在各种观点的废墟上未能形成几个强大的理论派别,离大秦帝国的一统华夏差得就更远了。而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必须从理论形态上把握认识对象,即用概念体系全面、系统地揭示该领域的本质和规律,零星、杂乱的观点并不构成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财产权法学还远不是一门科学,最多是科学的萌芽。
二、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
凡是在理论走入死胡同的时候,必然需要进行方法上的检讨;反之,理论上的建构必然需要方法上的创新。儘管方法并不就是理论本身,但却是理论的最深刻、最精华部分的沉澱物。从古到今,人们对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淮南子·说林训》中说“跬步不休,跛鳖千里”,意思是虽然不很聪明,但方法对头,也能成功。培根也说:“跛足而不迷路能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俄国着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
目前,在智慧财产权法研究领域中,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对智慧财产权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反思。“在研究过程当中,科学的方法是促成智慧财产权研究整体提升的重要途径。”
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智慧财产权法学理论,这就是智慧财产权方法论研究的根本意义。
可以想见:法学界同人第一次听到“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时,一般都会提出下列问题:如果智慧财产权法学存在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方法论,那幺物权法呢?债权法呢?是否也有着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物权法学方法论、债权法学方法论?可以说,这是一种经过良好专业训练才能产生的、近乎本能的学术反应。
拉德布鲁赫曾言:“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自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操心去知晓自身。”
我们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某一学科是病态的,则必须时刻进行反思,重视其自身方法论的研究,找出病症之所在。物权法学、债权法学中有着占据支配地位的基本理论,而且内部并无根本性的分歧,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範式,完成了体系化的历史性任务。当人们还没有对物权法中占据範式地位的理论产生质疑的时候,一般不会去思考这种理论的方法根源,自然就不会有方法论的争议。而一个病态的学科,里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甚至连像样的理论派别都没有,理论体系化任务远没有完成。这就需要对各种理论或观点所得以形成的方法进行考量,就需要探究理论建构的具体路径,方法论研究才有意义。也许物权法学、债权法学等健康的学科,有着完整的体系,所以暂时就没有方法论问题。
迄今为止,笔者只看到尹田教授写过一篇专门论述物权法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该文中,尹田教授将“概念法学”视为物权法研究的一种方法,考察其历史背景,并对其利弊进行了分析。而智慧财产权法学为“有病的学科”,面临着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任务,所以就需要方法论的研究。
上述分析大体上也适用于身份权法学。至于人格权法领域中,确实有着重大的分歧。比如,人格权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民法典中人格权部分是否应当独立成篇?等等。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论争双方如果各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论述,我们就能够发现各自运用的方法上的差异,就有可能形成人格权法学方法论。宋僧志文诗云:“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说不定,哪一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会发现枕边多了一本人格权法学方法论的专着。
概括言之,理论分歧源于方法上的分歧,只是在有着重大理论分歧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关注分歧的根源,才会去研究方法论问题。方法论研究既可以说是智慧财产权法学不幸之象徵,也可以说是智慧财产权法学幸运之标誌。它给予了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者建立新範式的历史性契机,而这种契机在民法其他领域中已经难得一见了。它促使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者必须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广泛地借鉴和汲取其他学科理论之精华,界定概念,总结规律,提炼原则,确立命题,建构範式,创立体系。对于广大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者而言,这是宿命,更是使命。
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有一句名言:“能做科研的都做着科研;那些不能做科研的就胡扯其方法论。”
这两种观点看似截然对立,其实不然。当既存的理论範式依然发挥效用的时候,我们在大师们的羽翼下,以收敛式思维从事常规科学的解谜工作,不需要去研究方法论问题。而在产生範式危机或是没有範式的时候,我们需要以发散性思维通过方法论研究去摧毁既存的理论範式,或是建构新的理论範式。
因此,方法论研究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各个学科中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刘春田教授认为:“中国智慧财产权的发展经过制度移植之后,正在步入理论论证,并已开始运用方法论的思考,其成果必能反哺智慧财产权制度。”
引自刘春田教授给杨雄文所着《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智慧财产权》一书所撰写的序言,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当前,方法论研究有助于形成各种智慧财产权理论派别,促进这些理论派别之间的良性竞争,然后在各种理论的废墟上,后继者可以构建起智慧财产权法学理论和制度体系的雄伟大厦。
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是不是妖怪,但搞不清楚是何方妖怪,仅凭自身的力量很难除之。如来佛更为厉害,能够算出妖怪的出处,因而降妖除魔的法力更为强大。在社会科学中,方法就是理论的出处,理论上的辩驳往往也需要上升到方法的层面上。一旦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上,很多“假理论”就如妖孽一样现出了原形。
第一节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一、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现状
在智慧财产权法研究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奇特的画面:
首先,上下脱节。在总论部分,有着众多观点分歧,智力成果权说、无形财产权说、信息产权说、符号产权说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观点往往高高在上,与分论部分脱节,不能够深入到各种智慧财产权制度内部,系统地指导各部门法的研究。
其次,左右不通。也就是说,分论部分研究彼此之间缺少有机的关联。比如,商标显着性、作品独创性、专利新颖性彼此之间有无关联?商标和作品、专利之间是什幺关係?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繫和区别是什幺?很少有人去进行专门的研究,分论部分之间常常呈现出一幅分疆裂土、各守领地、互不往来的景象。
最后,内外失调。对内,智慧财产权概念的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以至于只能用列举的方式对智慧财产权概念进行定义。对外,主要是与民法之间的关係失调。各种智慧财产权问题,比如外观设计、实用艺术品等智慧财产权对象是否受到多重保护?真的存在着所谓着作人格权吗?着作权人具有複製权、发行权、改编权等多种着作权财产权吗?如何解释智慧财产权权利穷竭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常常不符合民法的逻辑,往往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就此展开的各种观点基本上是在经验层面上各执一端,自说自话,莫衷一是,以至于智慧财产权法长期游离于民法体系之外。
整个智慧财产权法研究状况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王纲解纽,只存在着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如同智慧财产权总论部分之虚弱。而诸侯并起,纷争不已,又肖似智慧财产权分论中之争议。无论是身处智慧财产权法学界之内,还是置身其外,都能切实地感受到一个“乱”字。
为什幺会出现这种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何为理论以及如何建构智慧财产权理论。“倘法学能称之为科学,端在理论。”
引自刘春田教授给杨雄文所着《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智慧财产权》一书所撰写的序言,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从形式上看,理论是由基本概念、原理及各种推论构成的知识体系。库恩提出衡量理论优劣的5个标準: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理论应当符合下面几个标準:
(1)精确性。作为一个理论,或是需要来自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撑,或是需要翔实的经验实验材料的支持,或是二者兼备。比如,费孝通先生在对经验现象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提炼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差序格局等,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
(2)一致性。理论是用概念之网赋予世界以秩序,必须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而法学的生命一定是逻辑,而不是经验。法学中不能容忍经验层面上的观点纷争,必须形成一个内在协调一致的体系。
(3)广泛性。理论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应当儘可能地涵盖更多的现象。而理论越是抽象和巨观,就越能从整体上观察、思考研究对象的总体规律,越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牛顿正是凭藉着“神一般的思维力”,把巨观物体的机械运动都统一于万有引力。可以说,如果不脱离常识,不超越经验,就难以形成真正的理论。
(4)简单性。科学基础的逻辑简单性是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甚至可以说,简单往往是深刻的代名词。简单还是对理论进行审美的要求,“评价一个理论美不美,标準正是原理上的简单性,而不是技术上的困难性”
而要达致简单性,需要以儘可能少的前提条件作为建构理论的起点。比如,个体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等四个基本假设基础上,
在这些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推导出系统的理论。再如,爱因斯坦认为,物理科学的基础乃是“由最少数的概念和基本关係所组成,从它那里,可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各个分科的一切概念和一切关係”
(5)有效性。也就是说,理论经由一系列的中介,能够有效地进行演绎,由此形成的具体结论和命题能够切合实际,在自然科学中能够被实验所证实或证伪,在社会科学中能够产生具体的社会效果,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从理论自身存在状态上看,一定要具有广泛性,要脱离常识,超越经验,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理论。但从理论的效用上看,则需要能够联繫现实,指导实践,产生效果。
如果我们把理论比作一个人的话,精确性如同腿脚健壮、稳如磐石;一致性如同经脉畅通、气血调和;广泛性如同思维深邃、神目如电;简单性如同胖瘦适中、骨骼清奇;有效性则如同猿臂轻舒、十指灵巧。一个好的理论犹如古希腊着名雕塑家米隆所创作的“掷铁饼者”形象,给人以生命力爆发的震撼以及无尽的艺术享受。
掷铁饼者
用以上五个标準进行判断,我们会发现在目前智慧财产权法学总论部分,多数学说具备了广泛性、一致性、简单性三个特徵,但在精确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则参差不齐。有的观点,比如智力成果权说、无形财产权说等学说诉诸人的感官,既缺少强有力的支撑理论,也没有得到经验材料的支持,在精确性方面存在问题。另外,更为致命的是,绝大部分观点对于分则部分的研究并无多大的帮助,不能对商标显着性、作品独创性等核心概念作出富有意义的说明。这些观点本身既无法证实,也无从证伪,不能始终如一地去指导分论部分的研究,根本就缺少有效性。直接导致总论部分沦为空洞的议论,常常同智慧财产权实践分离,飘在半空下不来;而分论部分则流于经验的描述,往往与民法理论绝缘,趴在地上起不来。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儘管大部分智慧财产权教科书的总论言之凿凿,立论皇皇,一日弃之,除了使得教科书不至过于厚重以外,基本不会影响分论的学习。可以说,总论部分的玄学性与分论部分的经验性,构成诸多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缺陷。
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状况与我国古代科技极为类似。以医学为例,根据许倬云先生的看法,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把人的整个身体当作一个系统。但是从《本草纲目》和《伤寒论》两本书来看,中国医学可以脱离形上学的理论,而从实证上抽取经验,记录药物性质及病的现象。所以,中国医学实际上是两套东西来相配的,理论常常不过是点缀,医学的套用则是靠实际的检验所得出来的结果。农学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科学和技术是脱节的,科学沦为玄学,技术则流于经验,这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其名着《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经提出科学进步的三个阶段:一是前範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存在着各种理论派别,彼此纷争,莫衷一是;二是範式确立阶段。这个阶段中确立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方法、基本命题;三是危机阶段。旧的範式趋于崩溃,有待于建立新範式。库恩认为:“取得了一个範式,取得了範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誌。”
但是,智慧财产权法目前所处的阶段远没有达到前範式阶段。其中的原因在于:还没有哪一种观点能够演化为系统的理论,既能够统合自身,又能够指导实践。也就是说,在智慧财产权法学界,还没有从春秋诸侯纷争过渡到战国七雄争霸,在各种观点的废墟上未能形成几个强大的理论派别,离大秦帝国的一统华夏差得就更远了。而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必须从理论形态上把握认识对象,即用概念体系全面、系统地揭示该领域的本质和规律,零星、杂乱的观点并不构成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财产权法学还远不是一门科学,最多是科学的萌芽。
二、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
凡是在理论走入死胡同的时候,必然需要进行方法上的检讨;反之,理论上的建构必然需要方法上的创新。儘管方法并不就是理论本身,但却是理论的最深刻、最精华部分的沉澱物。从古到今,人们对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淮南子·说林训》中说“跬步不休,跛鳖千里”,意思是虽然不很聪明,但方法对头,也能成功。培根也说:“跛足而不迷路能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俄国着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
目前,在智慧财产权法研究领域中,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对智慧财产权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反思。“在研究过程当中,科学的方法是促成智慧财产权研究整体提升的重要途径。”
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智慧财产权法学理论,这就是智慧财产权方法论研究的根本意义。
可以想见:法学界同人第一次听到“智慧财产权法学方法论”时,一般都会提出下列问题:如果智慧财产权法学存在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方法论,那幺物权法呢?债权法呢?是否也有着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物权法学方法论、债权法学方法论?可以说,这是一种经过良好专业训练才能产生的、近乎本能的学术反应。
拉德布鲁赫曾言:“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自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操心去知晓自身。”
我们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某一学科是病态的,则必须时刻进行反思,重视其自身方法论的研究,找出病症之所在。物权法学、债权法学中有着占据支配地位的基本理论,而且内部并无根本性的分歧,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範式,完成了体系化的历史性任务。当人们还没有对物权法中占据範式地位的理论产生质疑的时候,一般不会去思考这种理论的方法根源,自然就不会有方法论的争议。而一个病态的学科,里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甚至连像样的理论派别都没有,理论体系化任务远没有完成。这就需要对各种理论或观点所得以形成的方法进行考量,就需要探究理论建构的具体路径,方法论研究才有意义。也许物权法学、债权法学等健康的学科,有着完整的体系,所以暂时就没有方法论问题。
迄今为止,笔者只看到尹田教授写过一篇专门论述物权法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该文中,尹田教授将“概念法学”视为物权法研究的一种方法,考察其历史背景,并对其利弊进行了分析。而智慧财产权法学为“有病的学科”,面临着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任务,所以就需要方法论的研究。
上述分析大体上也适用于身份权法学。至于人格权法领域中,确实有着重大的分歧。比如,人格权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民法典中人格权部分是否应当独立成篇?等等。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论争双方如果各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论述,我们就能够发现各自运用的方法上的差异,就有可能形成人格权法学方法论。宋僧志文诗云:“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说不定,哪一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会发现枕边多了一本人格权法学方法论的专着。
概括言之,理论分歧源于方法上的分歧,只是在有着重大理论分歧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关注分歧的根源,才会去研究方法论问题。方法论研究既可以说是智慧财产权法学不幸之象徵,也可以说是智慧财产权法学幸运之标誌。它给予了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者建立新範式的历史性契机,而这种契机在民法其他领域中已经难得一见了。它促使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者必须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广泛地借鉴和汲取其他学科理论之精华,界定概念,总结规律,提炼原则,确立命题,建构範式,创立体系。对于广大智慧财产权法学研究者而言,这是宿命,更是使命。
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有一句名言:“能做科研的都做着科研;那些不能做科研的就胡扯其方法论。”
这两种观点看似截然对立,其实不然。当既存的理论範式依然发挥效用的时候,我们在大师们的羽翼下,以收敛式思维从事常规科学的解谜工作,不需要去研究方法论问题。而在产生範式危机或是没有範式的时候,我们需要以发散性思维通过方法论研究去摧毁既存的理论範式,或是建构新的理论範式。
因此,方法论研究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各个学科中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刘春田教授认为:“中国智慧财产权的发展经过制度移植之后,正在步入理论论证,并已开始运用方法论的思考,其成果必能反哺智慧财产权制度。”
引自刘春田教授给杨雄文所着《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智慧财产权》一书所撰写的序言,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当前,方法论研究有助于形成各种智慧财产权理论派别,促进这些理论派别之间的良性竞争,然后在各种理论的废墟上,后继者可以构建起智慧财产权法学理论和制度体系的雄伟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