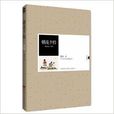《中外文学名着典藏系列:朝花夕拾》是2011年7月1日陕西师範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鲁迅。
基本介绍
- 书名:中外文学名着典藏系列:朝花夕拾
- 出版社:陕西师範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页数:224页
- 开本:16开
- 作者:鲁迅
- 出版日期:2011年7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561355978, 7561355971
内容简介
《朝花夕拾》特别收录了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记念》、《咬文嚼字》等在内的诸多鲁迅的精品文章。每篇文章都生动地向读者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之作。在刻画那些旧社会的不幸者时,鲁迅不仅仅是着眼于他们在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更多的是着眼于他们在精神上的麻木和愚昧。所以,这些文章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灵魂的伟大拷问。
《朝花夕拾》:鲁迅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他的文章笔锋犀利、针砭时弊,读后能发人深思。《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这本散文集在业内获有相当高的评价,是青年朋友们最热衷的书籍之一。我社为让读者能够读到更多更好的作品,便将鲁迅文章中的精华部分集结成册,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愉悦的读书享受,也同时将它推荐给广大中学生朋友。希望度过鲁迅的文章,能够让他们更清楚的了解社会、文化和生活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我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世界十大文豪之一,被誉为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着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吶喊》、《彷徨》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坟》等。其作品共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国小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专业推荐
媒体推荐
导读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破落士大夫家庭。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病痛,便改行提倡文艺运动。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o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範大学讲师o 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
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队《阿Q正传》等着名小说,并撰写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们内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1926年8月起先后任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旗帜,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生前出版小说集三种、散文集两种、杂文集十五种、通信集一种、文学史着作两种。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籍方面也成绩卓着。其全部着译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彙编为《鲁迅全集》(十六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四卷)。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共10篇。最初在《莽原》杂誌发表时总题目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集成书,改为现名。鲁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经受着北洋军阀当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1925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正人君子”们各种“流言”的攻击和诽谤。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鲁迅受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受守旧势力的排挤。在这样的处境中鲁迅曾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
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这10篇作品,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着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
《朝花夕拾》的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第一篇作品《狗·猫·鼠》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噑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阿长与》忆述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 --此文字指本书的不再付印或绝版版本。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破落士大夫家庭。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病痛,便改行提倡文艺运动。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o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範大学讲师o 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
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队《阿Q正传》等着名小说,并撰写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们内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1926年8月起先后任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旗帜,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生前出版小说集三种、散文集两种、杂文集十五种、通信集一种、文学史着作两种。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籍方面也成绩卓着。其全部着译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彙编为《鲁迅全集》(十六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四卷)。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共10篇。最初在《莽原》杂誌发表时总题目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集成书,改为现名。鲁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经受着北洋军阀当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1925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正人君子”们各种“流言”的攻击和诽谤。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鲁迅受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受守旧势力的排挤。在这样的处境中鲁迅曾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
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这10篇作品,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着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
《朝花夕拾》的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第一篇作品《狗·猫·鼠》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噑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阿长与》忆述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 --此文字指本书的不再付印或绝版版本。
名人推荐
由鲁迅最早的藏书想起
鲁迅最早的藏书,是一部木刻绘图《山海经》:四本小小的书,纸张很黄,刻印都十分粗拙,图像差到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可是年幼的鲁迅如获至宝: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怪物,远古神话世界的奇烈想像透过粗鄙的纸页喷薄而来,让心智初开的少年惊慕不已。几十年后,念及不知何时散佚的这最初的收藏,早已年过不惑的鲁迅在一册思忆儿时故乡生活的集子里写道,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这四本小书仅仅是一个起点。鲁迅的藏书单上随后添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从画》和《诗画舫》,又有了冠冕堂皇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曆钞传》,画的是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此外,《山海经》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红色的字,比早先那部精緻许多。少年鲁迅不仅多方搜罗,更炮製自家品牌的绘本: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摹,是他在三味书屋最愉快的消遣,尤其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鲁迅日后自谦地说,比如《蕩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各有一大本,后来卖给一个阔绰的同窗。
用学界近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来看,鲁迅自启蒙时代便表现出一种对“视觉文化”的偏爱。这种偏爱亦伴随他负笈东瀛,最突出的例证之一(“之一”二字或可删去),便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一段日俄战争期间的时事幻灯片,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捕获枪毙,一群中国人围观;影片之外,仙台医学院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自觉来到人生的转捩点。这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典故,在周蕾Primitive Passions一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鲁迅显然对给他带来巨大刺激的这种新兴媒介的本质认识不足,周蕾指出,不然他怎幺会在亲身体验了视觉影像的深刻震撼之后,反讽地做出投身文学的决定?作为电影领域的学者,周蕾的这一观察是敏锐而独到的。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文化研究多着眼于照片、电影、海报、月份牌及宣传广告等,其由此构建的“视觉文化”的概念,是否同样适用于或者说足够驾驭另一类从製造年代到性质都极为不同的视像文本,如绘图《西游记》、《玉曆钞传》甚至《山海经》?
关于鲁迅最早的藏书的故事收录于《朝花夕拾》。无论鲁迅如何被后世的文学史家塑造成一位鲜明而彻底的新文化的播种者与旧文化的掘墓人,一个读过其主要文学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及片段日记书信的细緻而诚实的读者,多少都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巍巍五千载文明传统的复调而暧昧的态度;尤其在他追忆儿时江浙岁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更让人一窥在新旧世界嬗替之际,最后一代为传统文化余晖所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与那个曾被无节制地神化英雄化经典化的鲁迅相比,我想,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正值盛年却自囚于幽僻的绍兴会馆一宿接一宿抄古碑抄佛经,那个重写中国小说史并对上古的神话寓言和宋以前的志怪传奇情有独钟,那个在支持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始终没有间断文言诗的创作,以及那个在四十岁上忆及故乡迎神赛会上的勾魂无常,亲切地称道其人情味够得上做一个“真正的朋友”的鲁迅。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吶喊》一书中谈到,概括地说,鲁迅在传统文化上的口味是在所谓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之外的,他的偏好更趋向于中国文化里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即与自孔孟到朱熹王阳明的儒家正统构成对立或保持疏离的思维与情感方式。举例来说,在小说文类里,鲁迅尤为唐以前、即宋明理学发端以前的作品所吸引,在诗人中他最倾心的是以瑰奇的想像和澎湃的灵魂诉求着称的屈原,以散文而言他推崇魏晋古风远胜唐宋八大家,以阅史而言他对野史杂说的兴味比对正史浓厚得多。
李欧梵以传统─反传统为轴丈量鲁迅相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定位,这种两极对立的视角本身便带有现代文学领域里根深蒂固的割裂与对抗的思维模式的烙印。然而针对“大传统”,还有另一种另类的可能,即“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自我身份意识清醒的、诉诸理智的“大传统”以文字书写为载体,通过在文史、思想与艺术上的不断构建表达出社会与文明总体的外露的理想;而未必自觉的、不倚赖思辩和书写的“小传统”寄身于不识字的阶层,并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信仰与行为惯式里滋衍不息──鲁迅的第一套藏书在更大意义上正是后者的一个缩影。更典型的是,这套绘图《山海经》不是从书店寻获的,而是鲁迅幼年的乳母,一个连自身名姓都未留下的下层女性在告假返乡时,不知从什幺地方弄来的。“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她这幺告诉鲁迅。长妈妈显然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在《朝花夕拾》另一处,鲁迅说,即便不识字如阿长,一看《二十四孝图》的图画也能滔滔讲出一段事迹。
YING
2011-01-05 08:53:15 --此文字指 平装 版本。
鲁迅最早的藏书,是一部木刻绘图《山海经》:四本小小的书,纸张很黄,刻印都十分粗拙,图像差到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可是年幼的鲁迅如获至宝: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怪物,远古神话世界的奇烈想像透过粗鄙的纸页喷薄而来,让心智初开的少年惊慕不已。几十年后,念及不知何时散佚的这最初的收藏,早已年过不惑的鲁迅在一册思忆儿时故乡生活的集子里写道,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这四本小书仅仅是一个起点。鲁迅的藏书单上随后添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从画》和《诗画舫》,又有了冠冕堂皇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曆钞传》,画的是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此外,《山海经》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红色的字,比早先那部精緻许多。少年鲁迅不仅多方搜罗,更炮製自家品牌的绘本: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摹,是他在三味书屋最愉快的消遣,尤其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鲁迅日后自谦地说,比如《蕩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各有一大本,后来卖给一个阔绰的同窗。
用学界近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来看,鲁迅自启蒙时代便表现出一种对“视觉文化”的偏爱。这种偏爱亦伴随他负笈东瀛,最突出的例证之一(“之一”二字或可删去),便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一段日俄战争期间的时事幻灯片,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捕获枪毙,一群中国人围观;影片之外,仙台医学院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自觉来到人生的转捩点。这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典故,在周蕾Primitive Passions一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鲁迅显然对给他带来巨大刺激的这种新兴媒介的本质认识不足,周蕾指出,不然他怎幺会在亲身体验了视觉影像的深刻震撼之后,反讽地做出投身文学的决定?作为电影领域的学者,周蕾的这一观察是敏锐而独到的。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文化研究多着眼于照片、电影、海报、月份牌及宣传广告等,其由此构建的“视觉文化”的概念,是否同样适用于或者说足够驾驭另一类从製造年代到性质都极为不同的视像文本,如绘图《西游记》、《玉曆钞传》甚至《山海经》?
关于鲁迅最早的藏书的故事收录于《朝花夕拾》。无论鲁迅如何被后世的文学史家塑造成一位鲜明而彻底的新文化的播种者与旧文化的掘墓人,一个读过其主要文学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及片段日记书信的细緻而诚实的读者,多少都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巍巍五千载文明传统的复调而暧昧的态度;尤其在他追忆儿时江浙岁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更让人一窥在新旧世界嬗替之际,最后一代为传统文化余晖所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与那个曾被无节制地神化英雄化经典化的鲁迅相比,我想,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正值盛年却自囚于幽僻的绍兴会馆一宿接一宿抄古碑抄佛经,那个重写中国小说史并对上古的神话寓言和宋以前的志怪传奇情有独钟,那个在支持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始终没有间断文言诗的创作,以及那个在四十岁上忆及故乡迎神赛会上的勾魂无常,亲切地称道其人情味够得上做一个“真正的朋友”的鲁迅。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吶喊》一书中谈到,概括地说,鲁迅在传统文化上的口味是在所谓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之外的,他的偏好更趋向于中国文化里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即与自孔孟到朱熹王阳明的儒家正统构成对立或保持疏离的思维与情感方式。举例来说,在小说文类里,鲁迅尤为唐以前、即宋明理学发端以前的作品所吸引,在诗人中他最倾心的是以瑰奇的想像和澎湃的灵魂诉求着称的屈原,以散文而言他推崇魏晋古风远胜唐宋八大家,以阅史而言他对野史杂说的兴味比对正史浓厚得多。
李欧梵以传统─反传统为轴丈量鲁迅相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定位,这种两极对立的视角本身便带有现代文学领域里根深蒂固的割裂与对抗的思维模式的烙印。然而针对“大传统”,还有另一种另类的可能,即“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自我身份意识清醒的、诉诸理智的“大传统”以文字书写为载体,通过在文史、思想与艺术上的不断构建表达出社会与文明总体的外露的理想;而未必自觉的、不倚赖思辩和书写的“小传统”寄身于不识字的阶层,并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信仰与行为惯式里滋衍不息──鲁迅的第一套藏书在更大意义上正是后者的一个缩影。更典型的是,这套绘图《山海经》不是从书店寻获的,而是鲁迅幼年的乳母,一个连自身名姓都未留下的下层女性在告假返乡时,不知从什幺地方弄来的。“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她这幺告诉鲁迅。长妈妈显然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在《朝花夕拾》另一处,鲁迅说,即便不识字如阿长,一看《二十四孝图》的图画也能滔滔讲出一段事迹。
YING
2011-01-05 08:53:15 --此文字指 平装 版本。
目录
朝花夕拾
小 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 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 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 记
时风诘论
记念刘和珍君
为了忘却的记念
“友邦惊诧”论
拿来主义
咬文嚼字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最艺术的国家
论“人言可畏”
论睁了眼看
文思博识
门外文谈
论新文字
灯下漫笔
运 命
文床秋梦
学界的三魂
论辩的魂灵
慧语睿辩
世故三昧
清明时节
说“面子”
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忆韦素园君
喝 茶
推的余谈
脸谱臆测
杂谈小品文
漫谈“漫画”
小 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 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 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 记
时风诘论
记念刘和珍君
为了忘却的记念
“友邦惊诧”论
拿来主义
咬文嚼字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最艺术的国家
论“人言可畏”
论睁了眼看
文思博识
门外文谈
论新文字
灯下漫笔
运 命
文床秋梦
学界的三魂
论辩的魂灵
慧语睿辩
世故三昧
清明时节
说“面子”
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忆韦素园君
喝 茶
推的余谈
脸谱臆测
杂谈小品文
漫谈“漫画”
文摘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樑,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幺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它。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幺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幺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幺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唯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餵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樑,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幺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它。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幺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幺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幺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唯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餵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后记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 “麻鬍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 “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 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 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 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蕃中皆畏惮, 其国婴儿啼者,以■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 胁云:薛尹来!鹹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 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方节度李丕即其 后。丕为重建碑。)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誌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蒐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 —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问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 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 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 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 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 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 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 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 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此文字指本书的不再付印或绝版版本。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蒐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 —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问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 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 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 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 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 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 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 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 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此文字指本书的不再付印或绝版版本。
序言
说明
《朝花夕拾》共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这些"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记录了作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成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这些篇章,往事与现实纠结,叙述与议论交织,情感深挚,笔调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见到鲁迅,问研究中国文学应该读什幺书,鲁迅即以《朝花夕拾》相赠。鲁迅1934年4月11日写信给想翻译此书的增田涉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
各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封面为陶元庆所绘。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3版有未名社和上海北新书局两个版本。
此次校订以鲁迅生前校定的版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注释力求简要。鲁迅时代某些词句和标点符号与现行用法不一致者,仍其旧,不做改动。 --此文字指 平装 版本。
《朝花夕拾》共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这些"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记录了作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成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这些篇章,往事与现实纠结,叙述与议论交织,情感深挚,笔调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见到鲁迅,问研究中国文学应该读什幺书,鲁迅即以《朝花夕拾》相赠。鲁迅1934年4月11日写信给想翻译此书的增田涉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
各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封面为陶元庆所绘。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3版有未名社和上海北新书局两个版本。
此次校订以鲁迅生前校定的版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注释力求简要。鲁迅时代某些词句和标点符号与现行用法不一致者,仍其旧,不做改动。 --此文字指 平装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