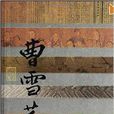一部《红楼梦》,集中国古典小说大成,奠定了曹雪芹在中国文化里不可取代的地位。曹雪芹一生跌宕的命运,凄凉的晚景,泣血着红楼而未能完成的遗憾,如此种种都让人感慨嗟叹。而曹雪芹自身的经历,对时代的见证,也让读者不停猜想,将他与“红楼梦中人”相对照,相索引。“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以极其饱满的激情,以对清代史学的熟稔,以对《红楼梦》了若指掌的取用,以考证辨析的大胆猜想与小心求证,写得这样一部在曹雪芹研究与红楼梦研究都不可或缺的传记。作品视野远阔,文字典雅,情怀悲悯,足可一读再读。
基本介绍
- 书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泣血红楼:曹雪芹传
-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 页数:510页
- 开本:16
- 品牌:作家出版社
- 作者:周汝昌 周伦玲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506371193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周汝昌是红学界的巨擘,单是不同时期所作曹雪芹的传记就有5种之多。《泣血红楼(曹雪芹传)》不仅是他一生红学和“曹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且是他此前诸种曹雪芹传的总汇,其考证精审,文字斐然可观。
作者既呈现了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淳美而精緻的文采,又富于诗人审慎的想像力和慈悲情怀。作品视野远阔,文字典雅,情怀悲悯,足可一读再读。
作者既呈现了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淳美而精緻的文采,又富于诗人审慎的想像力和慈悲情怀。作品视野远阔,文字典雅,情怀悲悯,足可一读再读。
作者简介
周汝昌(1918~2012),男,天津鹹水沽人。着名红学家、古典文学史家、诗人、书法家。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先后任燕京大学外国语文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第五届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着有《红楼梦新证》《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千秋一寸心》《永字八法》等。
名人推荐
作者既呈现了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淳美而精緻的文采,又富于诗人审慎的想像力和慈悲情怀。将几枚“曹雪芹碎片”复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动展示了小说家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精心铸造文学丰碑的心路与才智。
——文学专家张水舟
周汝昌是红学界的巨擘,单是不同时期所作营雪芹的传记就有5种之多。本传不仅是他一生红学和“曹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且是他此前诸种曹雪芹传的总汇,其考证精审,文字斐然可观。
——文学专家 刘炳来
——文学专家张水舟
周汝昌是红学界的巨擘,单是不同时期所作营雪芹的传记就有5种之多。本传不仅是他一生红学和“曹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且是他此前诸种曹雪芹传的总汇,其考证精审,文字斐然可观。
——文学专家 刘炳来
图书目录
001自题
001卷头语
005雪芹赋赞
001绪篇
010楔子
015第一章
065第二章
084第三章
091第四章
105第五章
118第六章
137第七章
160第八章
190第九章
235第十章
273第十一章
313第十二章
334不尽余音
434卷尾附编
493附录/曹雪芹生平年表
497后记(周伦玲)
001卷头语
005雪芹赋赞
001绪篇
010楔子
015第一章
065第二章
084第三章
091第四章
105第五章
118第六章
137第七章
160第八章
190第九章
235第十章
273第十一章
313第十二章
334不尽余音
434卷尾附编
493附录/曹雪芹生平年表
497后记(周伦玲)
后记
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的讯息时,已经是壬辰年的年尾了。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让我们感慨万千,因为这一年,父亲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成为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
今年三月中旬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按时听我们读报,突然一条讯息让他为之一振,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工程的公告。尤其让父亲高兴的是,这百位名人中竟然包括自己为之探索研究而追求奋斗了六十五年的曹雪芹这个名字。父亲说:“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见父亲高兴就凑到他耳边说:“那你一定得去申请!”父亲点点头,说:“好!一定,一定,你马上就去联繫吧!”过一会儿,又和我说:“你问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明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他们有没有播出一套节目的计画?”那天父亲很兴奋,浮想联翩,他在“筹划”该如何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
三月二十一日,我遵嘱给作协组委会的原文竹女士打电话,向她表达父亲準备参选曹雪芹的传记;而后又打电话给央视《百家讲坛》,询问是否有安排纪念曹雪芹的专题。电话那头传来孟庆吉先生的话,说还盼望父亲再来讲坛,当他听到父亲年高体弱时,很感慨说当初真应该为他多拍点儿影像资料。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中华读书报》上又传来这样一条讯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是秉承中央领导的意图由中国作家协会承办。此时父亲双目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昂起头,很留意这句话,让我们再读一遍。然后说:“这是个好契机,看来中央开始抓文化了!”
三月二十五日,农曆的三月初四——这一天是父亲的九十五岁大寿,俗称九五之尊。我们子女买来生日蛋糕和礼物,也有朋友前来祝寿,父亲很高兴。通常每年的农曆四月二十六日,父亲都要给曹雪芹过生日,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了,而今年父亲自己过生日,话题仍旧没离开曹雪芹——父亲说:“今天我的生日我很高兴,还是我的那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这曹雪芹传记,我要好好修订一下,明天就开始,你们先给我读一遍。”父亲指明要读的就是《文採风流曹雪芹》那本书。
(二)
父亲的治学旨归,说来十分有趣。他早年曾两次考取了燕京大学的西语系,这在燕大的校史上恐怕不多见。那时他的心愿是学好外文,待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着向世界传播。他早早地定下对陆机《文赋》的英译与研究的治学方向,也曾以《离骚》体译过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曾获得了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及师辈同仁热情而长时间的掌声。一位英籍教授说:“这样的论文远远地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
父亲在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考取了燕大中文系研究院,专攻中华古典文学,研究较多的则是唐诗和宋词。
一九四七年,由于和胡适的交往,父亲却走上了“治红”之途。父亲的研红工作实际是由“曹学”开端的,所付出的主要时间精力也集中在“曹学”——即雪芹的家世生平上。一九五三年父亲《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被专家评为“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着作”,父亲在这部书的“引论”中就早早给《红楼梦》和曹雪芹做了如下论断:
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义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国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亚,苏联人民一提到托尔斯泰而感到骄傲一样。我们中国人民也就以同样的骄傲感而念诵曹雪芹的名字。
父亲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结下了难捨难分的情缘,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于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上。
(三)
父亲把《红楼梦新证》寄给他的老师顾随先生。老师的回信给父亲以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之词,同时,老师明确提出:“述堂(顾随,号述堂)至盼玉言(周汝昌,字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并专此作诗,结篇的两句是:“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
……
(七)
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父亲的突然离去,中断了他修订《曹雪芹传》的计画,也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迨我们得到作家协会通知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半年之久了。
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要求,由我来接替父亲完成整理修订这部《曹雪芹传》的工作。抱着敬畏之情,丝毫不敢擅动父亲的一文一字,只是把父亲生前已经撰写完的、未成稿的、欲增入内容的相关文字,列入“不尽余言”一节。
按照作家协会的要求,这篇后记由我来撰写。我把这部传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向读者交代清楚。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知是否能够準确传达出父亲的意愿,也不知是否能达到这套丛书的要求,但是有一点可以告慰父亲,那就是他的遗愿完成了。
父亲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感谢知音友好的诸多帮助,感谢文星曹雪芹留下的巨着《红楼梦》。
最后,还是以父亲的诗篇作为结尾,诗曰:
为芹辛苦是何人?脂雪轩中笔不神。
病目自伤书读少,也能感悟贾和甄。
文採风流哪可传,悲欢离合事千端。
石头说法仁兼勇,莫认人间即梦间。
周伦玲
壬辰十一月十六
2012年12月27日
(一)
今年三月中旬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按时听我们读报,突然一条讯息让他为之一振,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工程的公告。尤其让父亲高兴的是,这百位名人中竟然包括自己为之探索研究而追求奋斗了六十五年的曹雪芹这个名字。父亲说:“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见父亲高兴就凑到他耳边说:“那你一定得去申请!”父亲点点头,说:“好!一定,一定,你马上就去联繫吧!”过一会儿,又和我说:“你问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明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他们有没有播出一套节目的计画?”那天父亲很兴奋,浮想联翩,他在“筹划”该如何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
三月二十一日,我遵嘱给作协组委会的原文竹女士打电话,向她表达父亲準备参选曹雪芹的传记;而后又打电话给央视《百家讲坛》,询问是否有安排纪念曹雪芹的专题。电话那头传来孟庆吉先生的话,说还盼望父亲再来讲坛,当他听到父亲年高体弱时,很感慨说当初真应该为他多拍点儿影像资料。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中华读书报》上又传来这样一条讯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是秉承中央领导的意图由中国作家协会承办。此时父亲双目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昂起头,很留意这句话,让我们再读一遍。然后说:“这是个好契机,看来中央开始抓文化了!”
三月二十五日,农曆的三月初四——这一天是父亲的九十五岁大寿,俗称九五之尊。我们子女买来生日蛋糕和礼物,也有朋友前来祝寿,父亲很高兴。通常每年的农曆四月二十六日,父亲都要给曹雪芹过生日,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了,而今年父亲自己过生日,话题仍旧没离开曹雪芹——父亲说:“今天我的生日我很高兴,还是我的那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这曹雪芹传记,我要好好修订一下,明天就开始,你们先给我读一遍。”父亲指明要读的就是《文採风流曹雪芹》那本书。
(二)
父亲的治学旨归,说来十分有趣。他早年曾两次考取了燕京大学的西语系,这在燕大的校史上恐怕不多见。那时他的心愿是学好外文,待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着向世界传播。他早早地定下对陆机《文赋》的英译与研究的治学方向,也曾以《离骚》体译过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曾获得了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及师辈同仁热情而长时间的掌声。一位英籍教授说:“这样的论文远远地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
父亲在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考取了燕大中文系研究院,专攻中华古典文学,研究较多的则是唐诗和宋词。
一九四七年,由于和胡适的交往,父亲却走上了“治红”之途。父亲的研红工作实际是由“曹学”开端的,所付出的主要时间精力也集中在“曹学”——即雪芹的家世生平上。一九五三年父亲《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被专家评为“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着作”,父亲在这部书的“引论”中就早早给《红楼梦》和曹雪芹做了如下论断:
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义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国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亚,苏联人民一提到托尔斯泰而感到骄傲一样。我们中国人民也就以同样的骄傲感而念诵曹雪芹的名字。
父亲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结下了难捨难分的情缘,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于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上。
(三)
父亲把《红楼梦新证》寄给他的老师顾随先生。老师的回信给父亲以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之词,同时,老师明确提出:“述堂(顾随,号述堂)至盼玉言(周汝昌,字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并专此作诗,结篇的两句是:“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
……
(七)
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父亲的突然离去,中断了他修订《曹雪芹传》的计画,也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迨我们得到作家协会通知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半年之久了。
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要求,由我来接替父亲完成整理修订这部《曹雪芹传》的工作。抱着敬畏之情,丝毫不敢擅动父亲的一文一字,只是把父亲生前已经撰写完的、未成稿的、欲增入内容的相关文字,列入“不尽余言”一节。
按照作家协会的要求,这篇后记由我来撰写。我把这部传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向读者交代清楚。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知是否能够準确传达出父亲的意愿,也不知是否能达到这套丛书的要求,但是有一点可以告慰父亲,那就是他的遗愿完成了。
父亲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感谢知音友好的诸多帮助,感谢文星曹雪芹留下的巨着《红楼梦》。
最后,还是以父亲的诗篇作为结尾,诗曰:
为芹辛苦是何人?脂雪轩中笔不神。
病目自伤书读少,也能感悟贾和甄。
文採风流哪可传,悲欢离合事千端。
石头说法仁兼勇,莫认人间即梦间。
周伦玲
壬辰十一月十六
2012年12月27日
序言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覆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採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採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澱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採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儘可能做到精緻、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后记:
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讯息时,已经是壬辰年的年尾了。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让我们感慨万千,因为这一年,父亲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成为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
今年三月中旬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按时听我们读报,突然一条讯息让他为之一振,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的公告。尤其让父亲高兴的是,这百位名人中竟然包括自己为之探索研究而追求奋斗了六十五年的曹雪芹这个名字。父亲说:“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见父亲高兴就凑到他耳边说:“那你一定得去申请!”父亲点点头,说:“好!一定,一定,你马上就去联繫吧!”过一会儿,又和我说:“你问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明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他们有没有播出一套节目的计画?”那天父亲很兴奋,浮想联翩,他在“筹划”该如何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
三月二十一日,我遵嘱给作协组委会的原文竹女士打电话,向她表达父亲準备参选曹雪芹的传记;而后又打电话给央视《百家讲坛》,询问是否有安排纪念曹雪芹的专题。电话那头传来孟庆吉先生的话,说还盼望父亲再来讲坛,当他听到父亲年高体弱时,很感慨说当初真应该为他多拍点儿影像资料。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中华读书报》上又传来这样一条讯息:“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是秉承中央领导的意图由中国作家协会承办。此时父亲双目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昂起头,很留意这句话,让我们再读一遍。然后说:“这是个好契机,看来中央开始抓文化了!”
三月二十五日,农曆的三月初四——这一天是父亲的九十五岁大寿,俗称九五之尊。我们子女买来生日蛋糕和礼物,也有朋友前来祝寿,父亲很高兴。通常每年的农曆四月二十六日,父亲都要给曹雪芹过生日,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了,而今年父亲自己过生日,话题仍旧没离开曹雪芹——父亲说:“今天我的生日我很高兴,还是我的那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这曹雪芹传记,我要好好修订一下,明天就开始,你们先给我读一遍。”父亲指明要读的就是《文採风流曹雪芹》那本书。
(二)
父亲的治学旨归,说来十分有趣。他早年曾两次考取了燕京大学的西语系,这在燕大的校史上恐怕不多见。那时他的心愿是学好外文,待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着向世界传播。他早早地定下对陆机《文赋》的英译与研究的治学方向,也曾以《离骚》体译过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曾获得了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及师辈同仁热情而长时间的掌声。一位英籍教授说:“这样的论文远远地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
父亲在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考取了燕大中文系研究院,专攻中华古典文学,研究较多的则是唐诗和宋词。
一九四七年,由于和胡适的交往,父亲却走上了“治红”之途。父亲的研红工作实际是由“曹学”开端的,所付出的主要时间精力也集中在“曹学”——即雪芹的家世生平上。一九五三年父亲《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被专家评为“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着作”,父亲在这部书的“引论”中就早早给《红楼梦》和曹雪芹做了如下论断:
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义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国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亚,苏联人民一提到托尔斯泰而感到骄傲一样。我们中国人民也就以同样的骄傲感而念诵曹雪芹的名字。
父亲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结下了难捨难分的情缘,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于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上。
(三)
父亲把《红楼梦新证》寄给他的老师顾随先生。老师的回信给父亲以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之词,同时,老师明确提出:“述堂(顾随,号述堂)至盼玉言(周汝昌,字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并专此作诗,结篇的两句是:“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①。”
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向无传记。对这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作者,父亲崇拜之至,敬仰之极!他甘愿“为芹辛苦”,立志为雪芹写一部传记。然而严格说来,“雪芹传”是无法写的,因为我们对这位作家的一生知道得太少了,其生平史料奇缺,根本没有足够的素材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传记。但是父亲认为:如果我们拿不出一部曹雪芹传来,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对世界人类文化,都是说不过去、难为人原谅的憾事。
记不得哪位学人说过: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就越会遭遇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而父亲也曾这样说过:如果你想要挑选一件最困难而最值得做、也最需要做的文化工作,那幺我请你挑选对中国最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的研究和评价。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他先后五次迎着困难奋进。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不久,便赶上一九五四年全国的《红楼梦》大讨论运动,此时的父亲被视为“胡适繁琐考证派”批评对象,学术处境十分尴尬。直到一九六二年,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热情的负责同志要父亲写一本介绍雪芹生平的小书,父亲因材料奇缺,困难重重,迟迟未能落笔。而后又再次受到鼓舞敦促,父亲才为盛意所感,再一次唤起了对“红学”“曹学”心情的复活。由此很快,一九六三年五月,稿即写成,就取名叫作《曹雪芹》,一九六四年四月出版。书只有十三万字,但从出版史上看,系统研究介绍曹雪芹的学术论着,这却算是第一部了。
其后,父亲用书册方式来介绍曹雪芹,先后又有过四次。
草创性的《曹雪芹》一书,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尽意畅怀。至七十年代末,父亲就将其修订扩充为《曹雪芹小传》,这是相当重要的改写,第一次将“正邪两赋”列为专章,此为小说哲理的核心课题。父亲从宋、明两代哲学家的天地生人“气稟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加以研讨,提出了与宋、明学者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悬殊而本质完全平等的进步思想,其“质”的飞跃有目共睹。美国着名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给这本《小传》作的序文中说:
作者採取了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
《小传》出版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好评,此书也一印再印,共发行了四十万册。于是父亲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
第三次试笔是在九十年代初。如果说《小传》具有更强的“科学性”,那幺《曹雪芹新传》则含有更多的“艺术性”。《新传》是特为世界读者写的,重点偏重于中国文化的顺带介绍。着名红学家梁归智先生说:
他在娓娓动人的叙述中,从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叠嶂层峦、烟云模糊处,托显出一个血肉丰满、鬚眉毕现的天才形象,展现了曹雪芹畸零不幸的一生。
而父亲是这样说的:
考古家掘得几枚碎陶片,运用他们的专门学识与技术技能“恢复”成一个“完整”的古陶罐,实在神奇!而我呢,所有的也只是几枚“曹雪芹”的碎片,却要把它们“恢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陶罐”——你看这难不难?我“恢复”成的,毕竟是个什幺?只有请读者给以估价了。只盼读者勿忘了一句话:介绍曹雪芹,其实就是为了介绍中华文化!
父亲认为曹雪芹的成就与品位,堪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的称号,而不只是世界一流小说作家。为了探讨这位中华异才的一切,包括祖源世系、氏族家风、生平身世,直到情理心灵、风流文采,他兢兢业业,锲而不捨。
九十年代末,父亲又开始了第四次为雪芹写传。记得这期间他曾大病一场,但始终没有放下撰写的工作。此传相对于以往的《小传》《新传》,展示出更多的特色。一是历史背景的时空涵盖面大为广阔;二是近年研索收穫有力地充实丰富了传主的生平经历;三是加强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艺术综合,读来更引人入胜。此次文笔特色还在于十分重视中华文学特有的诗境,在每一章的结束处,都有一首题跋的七绝,可歌可泣,以叹以咏。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二〇〇四年,父亲又出版了《曹雪芹画传》(赵华川先生绘图),这是他第五次为曹雪芹作传。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寻常的,坎坷困顿而又光辉灿烂。他讨人喜欢,受人爱恭倾赏,也大遭世俗的误解诽谤、排挤不容。他有老、庄的哲思,有屈原的《骚》愤,有司马迁的史才,有顾恺之的画艺和“痴绝”,有李义山、杜牧之风流才调,还有李龟年、黄旛绰的音乐、剧曲的天才功力……他一身兼有贵贱、荣辱、兴衰、离合、悲欢的人生阅历,又具备满族与汉族、江南与江北各种文化特色的融会综合之奇辉异彩。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形象。
这个形象非同小可,难以表现,可想而知。然而我要说:越是难于传达表现,才越是值得努力想方设法来传他、表他。
父亲为了曹雪芹而努力写作,不知休息,不计假日;又为了宁静,常常与冬夜寒宵结缘,夜深忍冻,独自走笔,习以为常,是苦是乐,也觉难分。他曾写下这样一首七律,从中可见其情景之一斑:
可是文星写照难,百重甘苦尽悲欢。
挑芹绿净知春动,浣玉丹新忆夜寒。
瀛海未周睽字义,心香长炷切毫端。
红楼历历灯痕永,未信人间抵梦间。
(四)
二〇〇九年,父亲那双濒于失明的眼睛终于全盲了,可是他的内心却依旧明亮。父亲常笑说自己是“文思泉涌,精神焕发”,写文章则题作“老而非骥,梦在千里”。
二〇一〇年,父亲“遇”到了两位知赏者。一位是刘再复先生,一位则是李泽厚先生。
二〇一〇年八月,着名学者刘再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天才,即最伟大的天才,而他的着作《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五十多年前,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认识就如此走上制高点,所以我称他为中国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然而,周先生作为知音还不仅是这一判断,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喜欢《三国演义》而热爱《红楼梦》,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全部生命、全部才华贡献给《红楼梦》研究。六十年钩沉探佚,六十年呕心沥血,六十年追求《红楼梦》真理,真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其中一节文字如下:
李:《茵梦湖》又怎能和《红楼梦》相比。对于《红楼梦》,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很有成就。他强调如把《红楼梦》归结为宝黛爱情,那就太简单了。他认为黛玉是沉塘自杀,死在宝钗结婚之前。我也觉得两宝的婚姻,因为是元春做主,没人能抗。姐姐的政治位势直接压倒个人,那给宝、黛、钗带来的是一种多幺複杂、沉重的情感。周汝昌论证宝玉和湘云最终结为夫妇,不然你没法解释“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还有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等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周说此书写的不仅是爱情而且是人情即人世间的各种感情。作者带着沉重的感伤来描述和珍惜人世间种种情感。一百二十回本写宝玉结婚的当天黛玉归天,具有戏剧性,可欣赏,但浅薄。周汝昌的探佚把整个境界提高了,使之有了更深沉的人世沧桑感,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展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大的政治变故对生活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以后也不再可能有什幺家道中兴了。所以我很同意可有两种《红楼梦》,一个是一百二十回,一个是八十回加探佚成果。后者境界高多了,情节也更真实,更大气。但可惜原着散佚了,作为艺术作品有缺陷。我不知道你们看《红楼梦》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发现,这部书不管你翻到哪一页,你都能看下去,这就奇怪啊!看《战争与和平》没有这感觉,有时还看不下去,儘管也是伟大作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这感觉,儘管极厉害,读来像心灵受了一次清洗似的。这使我想起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净化说”,与中国的审美感悟颇不相同。《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
两位先生的文章给了父亲很大鼓舞,父亲听读后,长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
父亲改变了以往自己的书写习惯,转为口述着述。一开始他很不适应,原来铺开稿纸就能落笔成章,而口述却让他不得不改变思维方式,“念”出来的文章没有了自己原来的风格和文采了,但父亲坚持做下去,常常是口述一篇文章要花好几天时间,最后还要读给他听。由于他听力极弱,我们常常大声叫喊,直令我们这几个六七十岁的子女都感觉吃不消,更何况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这对他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也许父亲已经感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已经悄悄临近,他在抓紧时间与生命赛跑。一次,父亲在接受採访时说:
我一点儿不休息,我不是说我九十多岁了,就该自由自在地过了,我每天工作不是说紧张,而是我要利用我那点儿可能的时间和精力,把每天不断思考的新问题、新见解铺到纸上,不铺到纸上,我自个儿也忘了。这个消失了谁也替代不了,会让我觉得这是我研究了六十年的损失。现在的写作是抢救性的,每天几百字也写,一千字也写,主题很分散,我这个人就是这幺贪得无厌。
仅二〇〇九年,父亲目盲后,就又连续出版了八部新着、几十篇新文均见诸报端杂誌。他口述的主题确实很分散,但万卷不离其宗——即中华文化这一大主题。例如,父亲认为:大观园一方面暗中继承了艮岳、万宁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继承了金谷园、桃李园的文化传统。在曹雪芹的《红楼梦》时代,满汉两大民族在万宁宫遗址上又有新的建筑,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如,由英国教育家提出儿童学习莎士比亚应从四岁开始为宜,父亲则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部巨着,其作者曹雪芹就相当于中国的莎士比亚,并倡议我国可以由国中一年级这个年龄开始引导学生接触《红楼梦》的概况或精神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花费很大精力口述出了一篇名为《娲皇:中华文化之母》的长文,父亲认为:娲皇的最大贡献是首先创出了“方”的图像与概念,矩尺则是她最为伟大的创造。父亲认为:《红楼梦》是以娲皇鍊石补天作为书的开端的。绝顶聪明的曹雪芹似乎早已悟知娲皇的最大贡献是在“圆”的大自然中创造了“方”的概念,所以才有那个“方经二十四丈,高经十二丈”的大石……
父亲最后出版的两本书,一本名为《红楼梦新境》,一本题作《寿芹心稿》,由这两个书名就不难看出父亲的心思所在。他把每天不断思考的新问题、新见解都铺到了纸上。父亲的计画中还要写一部关于《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写过,这幺多年过去了,他觉得与当时相比,应该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补充进去。直至今年五月中旬,父亲卧床不起了,还让我们给他读《红楼梦》;就在他离去的前两天,还口述了一部新书的大纲,书名暂定为《梦悟红楼》。但是,父亲最后思考了什幺,又有了哪些新的见解,却未能全部清晰地给我们留下。
(五)
父亲决定参选“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中的《曹雪芹传》,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父亲知道想找一个研究中华作家作品的方法是没有的,他早年引过孟子的话:“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那行吗?这个破折号不是孟子加的,是父亲加的,最后一句话补上了:“是以论其世也。”父亲说,你要了解真正的作品,你得先了解其人,你要想了解其人,可不要忘记了历史背景,是他那个时代、家世、环境、条件。父亲说:我应该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多做一些研究工作,然后才能谈得上真正读懂他的作品。父亲认为自己有三大优势:一是自己从事研究《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已历经六十五年,大多数第一手材料都是自己挖掘出来,有很多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几十部红学着作,具有可比性;第二是自己已经撰写过五次《曹雪芹传》,具有参加的资格和经历,具有可行性;第三点,就是他要为纪念这位文星巨匠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具有可能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党中央发出文化强国的号召,呼吁包容、创新的文化局面,父亲认为,这是一个宣传曹雪芹,弘扬中华文化最好的机遇。
父亲上述的理由很明了,也很直白,他希望修订后的这本书可读性更强一些,接受面更广一些。这期间父亲一面等待作家协会的回音,一面思考修订计画。
父亲说:若仅仅是罗列“事状”“行迹”,那纵使“史料丰富”“叙述详细”,也不等于理解那位传主的精神气质、衷曲性情。父亲希望修订时要把曹雪芹这个人物更加凸显出来,“可以允许循从某些线索痕迹加以合理推断,但不允许凭空‘想像’‘编造’一些‘故事情节’”。还说,若我有才力创作一部剧本或重写传记,那我就会决意“实现”以下几点:
一、皇帝知情《石头记》内容隐射政治内幕之后向雪芹逼索书稿时,雪芹气骨崚嶒,决不屈从;而此时雪芹之原配已逝,为了书稿的生命,不顾世俗的讥议,与其李氏表妹同居一处,雪芹将皇家搜剩的残稿重新补作与改写,表妹(脂砚)则一边协助抄整,一边朱笔批点——此为真本《石头记》之“私”传民间,正与皇家“组织写作班子”炮製的一百二十回伪“全本”抗争拚斗!
二、雪芹之逝,贫困、疾病、子殇、书佚……多层原因使他无力支撑,临终之境甚惨——此为史实,但不可一味渲染其境况之奇惨,只为一个“催人泪下”,那就将雪芹悲壮的一生弄成了一个“悲”而不壮的庸常小悲剧——那“悲”也就无法表现出一个真正深刻的大悲来。也就是说,就够不上悲剧的品格,陷于低级层次。
父亲曾经这样构想:若在萤屏“画面”上,结尾应该是“叠印”“闪回”雪芹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一生,然后映出一个崇高、伟大、风流文采而又傲骨嶙峋的形象来,并且这个形象永远隐现于燕(yān)郊西山的溪涧林泉之间,与日月山河,万古长存!
其实这项工作父亲早已在做了。早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父亲获聘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在颁发聘任证书的大会上,父亲令我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文化部蔡武部长,呼吁国家重视我国的第一天才小说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盼望借鉴一九六三年的纪念方式,儘早做好準备。不仅如此,父亲还找到自己的好友,拜託组织一批人撰写纪念文章,準备出一本纪念曹雪芹的文集。而父亲自己早在二〇一一年就已经开始口述了纪念文章。本书《不尽余音》一节中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名《创新与造化》,另一篇则曰《惓惓不尽》。
(六)
父亲一生多次得到党的关怀。一九五四年中宣部调其回京;一九七〇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由干校特调回京;一九八〇年,党中央再次给予父亲极大的关怀,蒙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将我从外地调回北京,正式担任父亲的研究助手,距今已经三十多年。目前我已经退休,但助理工作一直未曾间断。
在跟随父亲的工作中,感受最多的是父亲那种对中华文化的追求与热爱、痴情与执着。弘扬《红楼梦》中华文化永远是父亲的精神动力。父亲研究《红楼梦》数十年,常研常新,步步提升,非常人所能及。一九八六年父亲在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这一命题,倡议研究方向应以中华文化为其核心。一九九九年又进一步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二〇〇六年,父亲在接受台湾《联合报》採访时,又提出《红楼梦》应列为中华文化“第十四经”。父亲对《红楼梦》理解的深度、广度、境界在逐渐提升、发展,也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了解愈来愈深,他称曹雪芹为“伟大的思想家”“‘创教’的英雄哲士”。
近些年,时常听到有些人谈论自己经历时有这样的话:“我××岁就已经开始读《红楼梦》了。”不少人以读过《红楼梦》为自豪,而且年龄越小越感荣耀。殊不知,承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之前,权威的评价是它尚不足与世界一流的作品比肩并列。时见有评论者说是“某一两个人把《红楼梦》人为地‘拔高’起来的”,我始终怀疑这“某一两个人”能力怎会如此之巨大?
也时有人议论,说父亲一生就研究一本书,觉得很可笑也很费解;也有人对父亲的红学观点很不以为然;更有甚者,常常以人身攻击为能事。写至此,恰好莫言先生在诺奖上领奖,他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引在这里: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乾净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早在一九八四年,父亲曾撰有一首《自度曲》,词曰: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些魍魉蛇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铁;绿意凉,红情热。但提起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这是父亲一生最好的写照。父亲一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共出版着作六十多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九九八年,在父亲八十华诞、研红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发言,称父亲“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红学事业”,“为红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二〇〇七年,值父亲九十华诞、研红六十周年之际,刘延东同志又致贺函,称“尤在红学研究方面情有独钟,着作颇丰,享誉海内外,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七)
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父亲的突然离去,中断了他修订《曹雪芹传》的计画,也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迨我们得到作家协会通知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半年之久了。
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要求,由我来接替父亲完成整理修订这部《曹雪芹传》的工作。抱着敬畏之情,丝毫不敢擅动父亲的一文一字,只是把父亲生前已经撰写完的、未成稿的、欲增入内容的相关文字,列入“不尽余言”一节。
按照作家协会的要求,这篇后记由我来撰写。我把这部传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向读者交代清楚。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知是否能够準确传达出父亲的意愿,也不知是否能达到这套丛书的要求,但是有一点可以告慰父亲,那就是他的遗愿完成了。
父亲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感谢知音友好的诸多帮助,感谢文星曹雪芹留下的巨着《红楼梦》。
最后,还是以父亲的诗篇作为结尾,诗曰:
为芹辛苦是何人?脂雪轩中笔不神。
病目自伤书读少,也能感悟贾和甄。
文採风流哪可传,悲欢离合事千端。
石头说法仁兼勇,莫认人间即梦间。
周伦玲
壬辰十一月十六
2012年12月27日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覆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採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採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澱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採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儘可能做到精緻、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后记:
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讯息时,已经是壬辰年的年尾了。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让我们感慨万千,因为这一年,父亲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成为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
今年三月中旬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按时听我们读报,突然一条讯息让他为之一振,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的公告。尤其让父亲高兴的是,这百位名人中竟然包括自己为之探索研究而追求奋斗了六十五年的曹雪芹这个名字。父亲说:“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见父亲高兴就凑到他耳边说:“那你一定得去申请!”父亲点点头,说:“好!一定,一定,你马上就去联繫吧!”过一会儿,又和我说:“你问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明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他们有没有播出一套节目的计画?”那天父亲很兴奋,浮想联翩,他在“筹划”该如何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
三月二十一日,我遵嘱给作协组委会的原文竹女士打电话,向她表达父亲準备参选曹雪芹的传记;而后又打电话给央视《百家讲坛》,询问是否有安排纪念曹雪芹的专题。电话那头传来孟庆吉先生的话,说还盼望父亲再来讲坛,当他听到父亲年高体弱时,很感慨说当初真应该为他多拍点儿影像资料。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中华读书报》上又传来这样一条讯息:“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是秉承中央领导的意图由中国作家协会承办。此时父亲双目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昂起头,很留意这句话,让我们再读一遍。然后说:“这是个好契机,看来中央开始抓文化了!”
三月二十五日,农曆的三月初四——这一天是父亲的九十五岁大寿,俗称九五之尊。我们子女买来生日蛋糕和礼物,也有朋友前来祝寿,父亲很高兴。通常每年的农曆四月二十六日,父亲都要给曹雪芹过生日,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了,而今年父亲自己过生日,话题仍旧没离开曹雪芹——父亲说:“今天我的生日我很高兴,还是我的那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这曹雪芹传记,我要好好修订一下,明天就开始,你们先给我读一遍。”父亲指明要读的就是《文採风流曹雪芹》那本书。
(二)
父亲的治学旨归,说来十分有趣。他早年曾两次考取了燕京大学的西语系,这在燕大的校史上恐怕不多见。那时他的心愿是学好外文,待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着向世界传播。他早早地定下对陆机《文赋》的英译与研究的治学方向,也曾以《离骚》体译过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曾获得了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及师辈同仁热情而长时间的掌声。一位英籍教授说:“这样的论文远远地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
父亲在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考取了燕大中文系研究院,专攻中华古典文学,研究较多的则是唐诗和宋词。
一九四七年,由于和胡适的交往,父亲却走上了“治红”之途。父亲的研红工作实际是由“曹学”开端的,所付出的主要时间精力也集中在“曹学”——即雪芹的家世生平上。一九五三年父亲《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被专家评为“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着作”,父亲在这部书的“引论”中就早早给《红楼梦》和曹雪芹做了如下论断:
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义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国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亚,苏联人民一提到托尔斯泰而感到骄傲一样。我们中国人民也就以同样的骄傲感而念诵曹雪芹的名字。
父亲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结下了难捨难分的情缘,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于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上。
(三)
父亲把《红楼梦新证》寄给他的老师顾随先生。老师的回信给父亲以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之词,同时,老师明确提出:“述堂(顾随,号述堂)至盼玉言(周汝昌,字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并专此作诗,结篇的两句是:“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①。”
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向无传记。对这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作者,父亲崇拜之至,敬仰之极!他甘愿“为芹辛苦”,立志为雪芹写一部传记。然而严格说来,“雪芹传”是无法写的,因为我们对这位作家的一生知道得太少了,其生平史料奇缺,根本没有足够的素材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传记。但是父亲认为:如果我们拿不出一部曹雪芹传来,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对世界人类文化,都是说不过去、难为人原谅的憾事。
记不得哪位学人说过: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就越会遭遇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而父亲也曾这样说过:如果你想要挑选一件最困难而最值得做、也最需要做的文化工作,那幺我请你挑选对中国最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的研究和评价。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他先后五次迎着困难奋进。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不久,便赶上一九五四年全国的《红楼梦》大讨论运动,此时的父亲被视为“胡适繁琐考证派”批评对象,学术处境十分尴尬。直到一九六二年,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热情的负责同志要父亲写一本介绍雪芹生平的小书,父亲因材料奇缺,困难重重,迟迟未能落笔。而后又再次受到鼓舞敦促,父亲才为盛意所感,再一次唤起了对“红学”“曹学”心情的复活。由此很快,一九六三年五月,稿即写成,就取名叫作《曹雪芹》,一九六四年四月出版。书只有十三万字,但从出版史上看,系统研究介绍曹雪芹的学术论着,这却算是第一部了。
其后,父亲用书册方式来介绍曹雪芹,先后又有过四次。
草创性的《曹雪芹》一书,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尽意畅怀。至七十年代末,父亲就将其修订扩充为《曹雪芹小传》,这是相当重要的改写,第一次将“正邪两赋”列为专章,此为小说哲理的核心课题。父亲从宋、明两代哲学家的天地生人“气稟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加以研讨,提出了与宋、明学者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悬殊而本质完全平等的进步思想,其“质”的飞跃有目共睹。美国着名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给这本《小传》作的序文中说:
作者採取了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
《小传》出版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好评,此书也一印再印,共发行了四十万册。于是父亲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
第三次试笔是在九十年代初。如果说《小传》具有更强的“科学性”,那幺《曹雪芹新传》则含有更多的“艺术性”。《新传》是特为世界读者写的,重点偏重于中国文化的顺带介绍。着名红学家梁归智先生说:
他在娓娓动人的叙述中,从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叠嶂层峦、烟云模糊处,托显出一个血肉丰满、鬚眉毕现的天才形象,展现了曹雪芹畸零不幸的一生。
而父亲是这样说的:
考古家掘得几枚碎陶片,运用他们的专门学识与技术技能“恢复”成一个“完整”的古陶罐,实在神奇!而我呢,所有的也只是几枚“曹雪芹”的碎片,却要把它们“恢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陶罐”——你看这难不难?我“恢复”成的,毕竟是个什幺?只有请读者给以估价了。只盼读者勿忘了一句话:介绍曹雪芹,其实就是为了介绍中华文化!
父亲认为曹雪芹的成就与品位,堪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的称号,而不只是世界一流小说作家。为了探讨这位中华异才的一切,包括祖源世系、氏族家风、生平身世,直到情理心灵、风流文采,他兢兢业业,锲而不捨。
九十年代末,父亲又开始了第四次为雪芹写传。记得这期间他曾大病一场,但始终没有放下撰写的工作。此传相对于以往的《小传》《新传》,展示出更多的特色。一是历史背景的时空涵盖面大为广阔;二是近年研索收穫有力地充实丰富了传主的生平经历;三是加强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艺术综合,读来更引人入胜。此次文笔特色还在于十分重视中华文学特有的诗境,在每一章的结束处,都有一首题跋的七绝,可歌可泣,以叹以咏。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二〇〇四年,父亲又出版了《曹雪芹画传》(赵华川先生绘图),这是他第五次为曹雪芹作传。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寻常的,坎坷困顿而又光辉灿烂。他讨人喜欢,受人爱恭倾赏,也大遭世俗的误解诽谤、排挤不容。他有老、庄的哲思,有屈原的《骚》愤,有司马迁的史才,有顾恺之的画艺和“痴绝”,有李义山、杜牧之风流才调,还有李龟年、黄旛绰的音乐、剧曲的天才功力……他一身兼有贵贱、荣辱、兴衰、离合、悲欢的人生阅历,又具备满族与汉族、江南与江北各种文化特色的融会综合之奇辉异彩。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形象。
这个形象非同小可,难以表现,可想而知。然而我要说:越是难于传达表现,才越是值得努力想方设法来传他、表他。
父亲为了曹雪芹而努力写作,不知休息,不计假日;又为了宁静,常常与冬夜寒宵结缘,夜深忍冻,独自走笔,习以为常,是苦是乐,也觉难分。他曾写下这样一首七律,从中可见其情景之一斑:
可是文星写照难,百重甘苦尽悲欢。
挑芹绿净知春动,浣玉丹新忆夜寒。
瀛海未周睽字义,心香长炷切毫端。
红楼历历灯痕永,未信人间抵梦间。
(四)
二〇〇九年,父亲那双濒于失明的眼睛终于全盲了,可是他的内心却依旧明亮。父亲常笑说自己是“文思泉涌,精神焕发”,写文章则题作“老而非骥,梦在千里”。
二〇一〇年,父亲“遇”到了两位知赏者。一位是刘再复先生,一位则是李泽厚先生。
二〇一〇年八月,着名学者刘再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天才,即最伟大的天才,而他的着作《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五十多年前,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认识就如此走上制高点,所以我称他为中国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然而,周先生作为知音还不仅是这一判断,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喜欢《三国演义》而热爱《红楼梦》,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全部生命、全部才华贡献给《红楼梦》研究。六十年钩沉探佚,六十年呕心沥血,六十年追求《红楼梦》真理,真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其中一节文字如下:
李:《茵梦湖》又怎能和《红楼梦》相比。对于《红楼梦》,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很有成就。他强调如把《红楼梦》归结为宝黛爱情,那就太简单了。他认为黛玉是沉塘自杀,死在宝钗结婚之前。我也觉得两宝的婚姻,因为是元春做主,没人能抗。姐姐的政治位势直接压倒个人,那给宝、黛、钗带来的是一种多幺複杂、沉重的情感。周汝昌论证宝玉和湘云最终结为夫妇,不然你没法解释“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还有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等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周说此书写的不仅是爱情而且是人情即人世间的各种感情。作者带着沉重的感伤来描述和珍惜人世间种种情感。一百二十回本写宝玉结婚的当天黛玉归天,具有戏剧性,可欣赏,但浅薄。周汝昌的探佚把整个境界提高了,使之有了更深沉的人世沧桑感,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展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大的政治变故对生活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以后也不再可能有什幺家道中兴了。所以我很同意可有两种《红楼梦》,一个是一百二十回,一个是八十回加探佚成果。后者境界高多了,情节也更真实,更大气。但可惜原着散佚了,作为艺术作品有缺陷。我不知道你们看《红楼梦》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发现,这部书不管你翻到哪一页,你都能看下去,这就奇怪啊!看《战争与和平》没有这感觉,有时还看不下去,儘管也是伟大作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这感觉,儘管极厉害,读来像心灵受了一次清洗似的。这使我想起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净化说”,与中国的审美感悟颇不相同。《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
两位先生的文章给了父亲很大鼓舞,父亲听读后,长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
父亲改变了以往自己的书写习惯,转为口述着述。一开始他很不适应,原来铺开稿纸就能落笔成章,而口述却让他不得不改变思维方式,“念”出来的文章没有了自己原来的风格和文采了,但父亲坚持做下去,常常是口述一篇文章要花好几天时间,最后还要读给他听。由于他听力极弱,我们常常大声叫喊,直令我们这几个六七十岁的子女都感觉吃不消,更何况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这对他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也许父亲已经感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已经悄悄临近,他在抓紧时间与生命赛跑。一次,父亲在接受採访时说:
我一点儿不休息,我不是说我九十多岁了,就该自由自在地过了,我每天工作不是说紧张,而是我要利用我那点儿可能的时间和精力,把每天不断思考的新问题、新见解铺到纸上,不铺到纸上,我自个儿也忘了。这个消失了谁也替代不了,会让我觉得这是我研究了六十年的损失。现在的写作是抢救性的,每天几百字也写,一千字也写,主题很分散,我这个人就是这幺贪得无厌。
仅二〇〇九年,父亲目盲后,就又连续出版了八部新着、几十篇新文均见诸报端杂誌。他口述的主题确实很分散,但万卷不离其宗——即中华文化这一大主题。例如,父亲认为:大观园一方面暗中继承了艮岳、万宁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继承了金谷园、桃李园的文化传统。在曹雪芹的《红楼梦》时代,满汉两大民族在万宁宫遗址上又有新的建筑,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如,由英国教育家提出儿童学习莎士比亚应从四岁开始为宜,父亲则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部巨着,其作者曹雪芹就相当于中国的莎士比亚,并倡议我国可以由国中一年级这个年龄开始引导学生接触《红楼梦》的概况或精神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花费很大精力口述出了一篇名为《娲皇:中华文化之母》的长文,父亲认为:娲皇的最大贡献是首先创出了“方”的图像与概念,矩尺则是她最为伟大的创造。父亲认为:《红楼梦》是以娲皇鍊石补天作为书的开端的。绝顶聪明的曹雪芹似乎早已悟知娲皇的最大贡献是在“圆”的大自然中创造了“方”的概念,所以才有那个“方经二十四丈,高经十二丈”的大石……
父亲最后出版的两本书,一本名为《红楼梦新境》,一本题作《寿芹心稿》,由这两个书名就不难看出父亲的心思所在。他把每天不断思考的新问题、新见解都铺到了纸上。父亲的计画中还要写一部关于《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写过,这幺多年过去了,他觉得与当时相比,应该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补充进去。直至今年五月中旬,父亲卧床不起了,还让我们给他读《红楼梦》;就在他离去的前两天,还口述了一部新书的大纲,书名暂定为《梦悟红楼》。但是,父亲最后思考了什幺,又有了哪些新的见解,却未能全部清晰地给我们留下。
(五)
父亲决定参选“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中的《曹雪芹传》,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父亲知道想找一个研究中华作家作品的方法是没有的,他早年引过孟子的话:“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那行吗?这个破折号不是孟子加的,是父亲加的,最后一句话补上了:“是以论其世也。”父亲说,你要了解真正的作品,你得先了解其人,你要想了解其人,可不要忘记了历史背景,是他那个时代、家世、环境、条件。父亲说:我应该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多做一些研究工作,然后才能谈得上真正读懂他的作品。父亲认为自己有三大优势:一是自己从事研究《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已历经六十五年,大多数第一手材料都是自己挖掘出来,有很多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几十部红学着作,具有可比性;第二是自己已经撰写过五次《曹雪芹传》,具有参加的资格和经历,具有可行性;第三点,就是他要为纪念这位文星巨匠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具有可能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党中央发出文化强国的号召,呼吁包容、创新的文化局面,父亲认为,这是一个宣传曹雪芹,弘扬中华文化最好的机遇。
父亲上述的理由很明了,也很直白,他希望修订后的这本书可读性更强一些,接受面更广一些。这期间父亲一面等待作家协会的回音,一面思考修订计画。
父亲说:若仅仅是罗列“事状”“行迹”,那纵使“史料丰富”“叙述详细”,也不等于理解那位传主的精神气质、衷曲性情。父亲希望修订时要把曹雪芹这个人物更加凸显出来,“可以允许循从某些线索痕迹加以合理推断,但不允许凭空‘想像’‘编造’一些‘故事情节’”。还说,若我有才力创作一部剧本或重写传记,那我就会决意“实现”以下几点:
一、皇帝知情《石头记》内容隐射政治内幕之后向雪芹逼索书稿时,雪芹气骨崚嶒,决不屈从;而此时雪芹之原配已逝,为了书稿的生命,不顾世俗的讥议,与其李氏表妹同居一处,雪芹将皇家搜剩的残稿重新补作与改写,表妹(脂砚)则一边协助抄整,一边朱笔批点——此为真本《石头记》之“私”传民间,正与皇家“组织写作班子”炮製的一百二十回伪“全本”抗争拚斗!
二、雪芹之逝,贫困、疾病、子殇、书佚……多层原因使他无力支撑,临终之境甚惨——此为史实,但不可一味渲染其境况之奇惨,只为一个“催人泪下”,那就将雪芹悲壮的一生弄成了一个“悲”而不壮的庸常小悲剧——那“悲”也就无法表现出一个真正深刻的大悲来。也就是说,就够不上悲剧的品格,陷于低级层次。
父亲曾经这样构想:若在萤屏“画面”上,结尾应该是“叠印”“闪回”雪芹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一生,然后映出一个崇高、伟大、风流文采而又傲骨嶙峋的形象来,并且这个形象永远隐现于燕(yān)郊西山的溪涧林泉之间,与日月山河,万古长存!
其实这项工作父亲早已在做了。早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父亲获聘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在颁发聘任证书的大会上,父亲令我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文化部蔡武部长,呼吁国家重视我国的第一天才小说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盼望借鉴一九六三年的纪念方式,儘早做好準备。不仅如此,父亲还找到自己的好友,拜託组织一批人撰写纪念文章,準备出一本纪念曹雪芹的文集。而父亲自己早在二〇一一年就已经开始口述了纪念文章。本书《不尽余音》一节中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名《创新与造化》,另一篇则曰《惓惓不尽》。
(六)
父亲一生多次得到党的关怀。一九五四年中宣部调其回京;一九七〇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由干校特调回京;一九八〇年,党中央再次给予父亲极大的关怀,蒙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将我从外地调回北京,正式担任父亲的研究助手,距今已经三十多年。目前我已经退休,但助理工作一直未曾间断。
在跟随父亲的工作中,感受最多的是父亲那种对中华文化的追求与热爱、痴情与执着。弘扬《红楼梦》中华文化永远是父亲的精神动力。父亲研究《红楼梦》数十年,常研常新,步步提升,非常人所能及。一九八六年父亲在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这一命题,倡议研究方向应以中华文化为其核心。一九九九年又进一步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二〇〇六年,父亲在接受台湾《联合报》採访时,又提出《红楼梦》应列为中华文化“第十四经”。父亲对《红楼梦》理解的深度、广度、境界在逐渐提升、发展,也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了解愈来愈深,他称曹雪芹为“伟大的思想家”“‘创教’的英雄哲士”。
近些年,时常听到有些人谈论自己经历时有这样的话:“我××岁就已经开始读《红楼梦》了。”不少人以读过《红楼梦》为自豪,而且年龄越小越感荣耀。殊不知,承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之前,权威的评价是它尚不足与世界一流的作品比肩并列。时见有评论者说是“某一两个人把《红楼梦》人为地‘拔高’起来的”,我始终怀疑这“某一两个人”能力怎会如此之巨大?
也时有人议论,说父亲一生就研究一本书,觉得很可笑也很费解;也有人对父亲的红学观点很不以为然;更有甚者,常常以人身攻击为能事。写至此,恰好莫言先生在诺奖上领奖,他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引在这里: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乾净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早在一九八四年,父亲曾撰有一首《自度曲》,词曰: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些魍魉蛇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铁;绿意凉,红情热。但提起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这是父亲一生最好的写照。父亲一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共出版着作六十多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九九八年,在父亲八十华诞、研红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发言,称父亲“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红学事业”,“为红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二〇〇七年,值父亲九十华诞、研红六十周年之际,刘延东同志又致贺函,称“尤在红学研究方面情有独钟,着作颇丰,享誉海内外,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七)
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父亲的突然离去,中断了他修订《曹雪芹传》的计画,也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迨我们得到作家协会通知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半年之久了。
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要求,由我来接替父亲完成整理修订这部《曹雪芹传》的工作。抱着敬畏之情,丝毫不敢擅动父亲的一文一字,只是把父亲生前已经撰写完的、未成稿的、欲增入内容的相关文字,列入“不尽余言”一节。
按照作家协会的要求,这篇后记由我来撰写。我把这部传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向读者交代清楚。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知是否能够準确传达出父亲的意愿,也不知是否能达到这套丛书的要求,但是有一点可以告慰父亲,那就是他的遗愿完成了。
父亲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感谢知音友好的诸多帮助,感谢文星曹雪芹留下的巨着《红楼梦》。
最后,还是以父亲的诗篇作为结尾,诗曰:
为芹辛苦是何人?脂雪轩中笔不神。
病目自伤书读少,也能感悟贾和甄。
文採风流哪可传,悲欢离合事千端。
石头说法仁兼勇,莫认人间即梦间。
周伦玲
壬辰十一月十六
2012年12月27日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泣血红楼:曹雪芹传》中作者採取了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展示了小说家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精心铸造文学丰碑的心路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