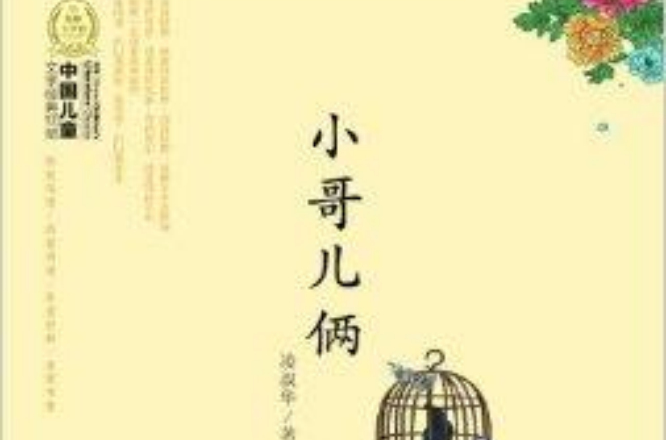《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小哥儿俩》以《小哥儿俩》初版为底本,保留《小哥儿俩》《搬家》《小蛤蟆》《凤凰》《弟弟》《小英》《千代子》《开瑟琳》和《生日》等9篇“小孩子的作品”,删去《倪云林》《写信》《无聊》和《异国》等4篇“另一类的东西”,加入童话《红了的冬青》和《小床与水塔》《一件喜事》《一个故事》《八月节》《阿昭》《中国儿女》等6篇以儿童为主角或以儿童视角来叙事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充分显示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及其独到的写作风格,非常值得欣赏。
基本介绍
- 书名: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小哥儿俩
-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 页数:216页
- 开本:16
- 作者:凌叔华
- 出版日期:2011年2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7535163505, 9787535163509
内容简介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小哥儿俩》推荐:凌叔华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是其中第四位夫人所生,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后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都有优异的成就。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小哥儿俩》为她的短篇小说集,主要收录了《小蛤蟆》、《搬家》、《千代子》、《小床与水塔》、《红了的冬青》、《一个故事》、《中国儿女》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阅读文学经典,也像大海茫茫之中的水手在航海,书中的忧愁与悲伤,是他的黑夜和风暴;书中的欢乐与希望,是他的阳光和云彩。世界上还有比阅读更美好、更惬意、更幸福的事情吗?请你相信:你阅读,所以你更美丽;正如你思想,所以你存在。
阅读经典,就是阅读世界,阅读经典,就像水手去航海、你的忧愁,就是我的风暴,你的欢乐,就是我的云彩、能做一名读者是幸福的我阅读,所以我美丽,我阅读,所以我存在。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小哥儿俩》为她的短篇小说集,主要收录了《小蛤蟆》、《搬家》、《千代子》、《小床与水塔》、《红了的冬青》、《一个故事》、《中国儿女》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阅读文学经典,也像大海茫茫之中的水手在航海,书中的忧愁与悲伤,是他的黑夜和风暴;书中的欢乐与希望,是他的阳光和云彩。世界上还有比阅读更美好、更惬意、更幸福的事情吗?请你相信:你阅读,所以你更美丽;正如你思想,所以你存在。
阅读经典,就是阅读世界,阅读经典,就像水手去航海、你的忧愁,就是我的风暴,你的欢乐,就是我的云彩、能做一名读者是幸福的我阅读,所以我美丽,我阅读,所以我存在。
图书目录
小哥儿俩
搬家
小蛤蟆
凤凰
弟弟
小英
千代子
开瑟琳
生日
小床与水塔
红了的冬青
一件喜事
一个故事
八月节
阿昭
中国儿女
附录一 再谈儿童文学
附录二 论自然画与人物画
编后记
搬家
小蛤蟆
凤凰
弟弟
小英
千代子
开瑟琳
生日
小床与水塔
红了的冬青
一件喜事
一个故事
八月节
阿昭
中国儿女
附录一 再谈儿童文学
附录二 论自然画与人物画
编后记
后记
凌叔华,原名凌瑞唐,笔名瑞棠、素心、素华等。1900年3月25日出生于北京,原籍广东番禺。从七八岁起,就从师学画。1909年,随父亲凌福彭赴日本京都。1919年,进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範学校。1921年,入燕京大学。1924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1926年,与陈源(西滢)结婚。1927年,在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花之寺》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1929年,随丈夫到武汉大学,后与袁昌英、苏雪林并称为“珞珈三杰”。1930年,短篇小说集《女人》和《小孩》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应约主编《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同年,《小孩》改名《小哥儿俩》,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1938年初,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1939年底,北上奔母丧,后留居北平,执教于燕京大学。1941年底,离开北平。1942年初,抵达乐山。1945年,《小哥儿俩》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再版。凌叔华曾请朱光潜写过一篇序文,但未用。1947年,定居英国。1953年,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由英国荷盖斯出版社出版。1956年,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8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同年,文集《爱山庐梦影》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出版。1969年,返回英国。1989年,回到中国。1990年5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小哥儿俩》出版之前,即1935年9月,凌叔华写过一篇自序,全文如下:
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本书篇幅少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面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的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但为书局打算,这也说不得了。
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幺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麻烦。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如这本小书能引起几个读者重温理一下旧梦,作者也就得到很大的酬报了。
本书以《小哥儿俩》初版为底本,保留《小哥儿俩》《搬家》《小蛤蟆》《凤凰》《弟弟》《小英》《千代子》《开瑟琳》和《生日》等9篇“小孩子的作品”,删去《倪云林》《写信》《无聊》和《异国》等4篇“另一类的东西”,加入童话《红了的冬青》和《小床与水塔》《一件喜事》《一个故事》《八月节》《阿昭》《中国儿女》等6篇以儿童为主角或以儿童视角来叙事的作品,仍旧沿用这个影响很大而且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书名。
凌叔华之所以把其做品里的“小人儿”看做是她“心窝上的安琪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她“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她曾在1939年所发表的演讲《在文学里的儿童》中说:“我自己大约属于偏爱儿童的那一种人,长大成人后,我的兴趣常常与儿童很近。在玩意店里或摊子上,我看了要买,买了又看,常站上一两个钟头。一堆小孩子在那里玩笑,我虽不能参加,但是在旁守着,向来没感乏味儿。”(《文学集林》1940年1月第4辑)还说她写作儿童小说,是一种享受,一种愉快的工作。正因为凌叔华偏爱儿童,有与儿童相近的兴趣,所以她的笔触能够深入到儿童的心灵世界,写出大乖、二乖、枝儿、“弟弟”、小英、千代子、开瑟琳、晶子等众多个性鲜明,年龄与其思想、行为、心理大体相称的“小人儿”来。如果说叶圣陶、张天翼等人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观察儿童生活的结果”(惕即茅盾《再谈儿童文学》,《文学》月刊1936年1月1日第6卷第1号)的话,那幺,凌叔华的儿童文学作品则是用心感受儿童生活的结果。
《中国儿女》是凌叔华仅有的一部中篇小说,创作于抗战中期。这部小说与凌叔华此前的作品相比,在题材上有较大变化,标誌着作者已将视线由“高门巨族”的深深庭院投向窗外血与火的苦难世界。抗战爆发以后,凌叔华关注国家的前途,更关心儿童的命运,并为此做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工作。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凌叔华被聘为名誉理事。同年5月18日为国际儿童亲善节,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邀集武汉地区的5岁至14岁中外儿童约180人,在海军青年会举行庆祝大会。大会由凌叔华主持并致欢迎词,她呼吁与会同志“勿忘怀现在受难之中国儿童”,“此后多做救济中国难童工作”(《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会务简讯》,《世界政治》半月刊1938年6月15日第3卷第2期)。针对大量无辜儿童被日军战机炸死炸伤的惨状,凌叔华写过一篇题为《为接近战区及被轰炸区域的儿童说的话》的文章,希望“把接近战地以及有被轰炸危险的城市或村镇中的儿童儘量收集,尽力把他们移送较为安全的地带”,“最好能教养他们,使其在抗战岁月中,身心仍得良善发育,为国家製造一些未来的良善有用的国民,使他们成为我们复兴的一批台柱子”(《新民族》周刊1938年11月22日第2卷第18期)。1942年,她曾购买近千元床桌罩等手工艺品,寄往美国,请胡适帮忙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内地战时儿童保育院。凌叔华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儿童倾注了爱心,也寄予了厚望。在《中国儿女》这部小说中,她借建国、徐廉、宛英等几个“中国儿女”,表达了自己抗战救亡的爱国热情,同时把复兴国家的希望放在他们这些未来的“台柱子”身上。
《阿昭》原载《燕大月刊》1928年1月12日第1卷第4期,目录页署名凌叔华女士,内页标题下署名叔华,文末说明是“录1924年旧作”。凌叔华的小说多以女性和儿童为主角,这篇小说则运用儿童视角,集中“回忆”了“我童年最感兴味的一个人”,一个厨师,一个“三十来岁”的男性。这在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中也可算是“另类”。《阿昭》是凌叔华的一篇逸文,在已经出版的各种作品集中都未见收录。
凌叔华既是作家,也是画家。总体来看,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情节比较单一,结构比较单纯,具有一种“写意画”的特点。正如朱光潜所说的:“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论自然画与人物画——凌叔华作〈小哥儿俩〉序》,《天下周刊》1946年5月5日创刊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中的作品,除个别文字(如“的”等)和标点依据现行用法酌予改动外,其余皆一仍其旧;本书是我和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先生合作编订的;感谢凌叔华研究专家陈学勇先生,我们在选定篇目时曾得到他的热情指导和帮助。
陈建军
2009年12月2日于珞珈山麓
《小哥儿俩》出版之前,即1935年9月,凌叔华写过一篇自序,全文如下:
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本书篇幅少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面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的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但为书局打算,这也说不得了。
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幺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麻烦。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如这本小书能引起几个读者重温理一下旧梦,作者也就得到很大的酬报了。
本书以《小哥儿俩》初版为底本,保留《小哥儿俩》《搬家》《小蛤蟆》《凤凰》《弟弟》《小英》《千代子》《开瑟琳》和《生日》等9篇“小孩子的作品”,删去《倪云林》《写信》《无聊》和《异国》等4篇“另一类的东西”,加入童话《红了的冬青》和《小床与水塔》《一件喜事》《一个故事》《八月节》《阿昭》《中国儿女》等6篇以儿童为主角或以儿童视角来叙事的作品,仍旧沿用这个影响很大而且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书名。
凌叔华之所以把其做品里的“小人儿”看做是她“心窝上的安琪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她“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她曾在1939年所发表的演讲《在文学里的儿童》中说:“我自己大约属于偏爱儿童的那一种人,长大成人后,我的兴趣常常与儿童很近。在玩意店里或摊子上,我看了要买,买了又看,常站上一两个钟头。一堆小孩子在那里玩笑,我虽不能参加,但是在旁守着,向来没感乏味儿。”(《文学集林》1940年1月第4辑)还说她写作儿童小说,是一种享受,一种愉快的工作。正因为凌叔华偏爱儿童,有与儿童相近的兴趣,所以她的笔触能够深入到儿童的心灵世界,写出大乖、二乖、枝儿、“弟弟”、小英、千代子、开瑟琳、晶子等众多个性鲜明,年龄与其思想、行为、心理大体相称的“小人儿”来。如果说叶圣陶、张天翼等人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观察儿童生活的结果”(惕即茅盾《再谈儿童文学》,《文学》月刊1936年1月1日第6卷第1号)的话,那幺,凌叔华的儿童文学作品则是用心感受儿童生活的结果。
《中国儿女》是凌叔华仅有的一部中篇小说,创作于抗战中期。这部小说与凌叔华此前的作品相比,在题材上有较大变化,标誌着作者已将视线由“高门巨族”的深深庭院投向窗外血与火的苦难世界。抗战爆发以后,凌叔华关注国家的前途,更关心儿童的命运,并为此做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工作。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凌叔华被聘为名誉理事。同年5月18日为国际儿童亲善节,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邀集武汉地区的5岁至14岁中外儿童约180人,在海军青年会举行庆祝大会。大会由凌叔华主持并致欢迎词,她呼吁与会同志“勿忘怀现在受难之中国儿童”,“此后多做救济中国难童工作”(《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会务简讯》,《世界政治》半月刊1938年6月15日第3卷第2期)。针对大量无辜儿童被日军战机炸死炸伤的惨状,凌叔华写过一篇题为《为接近战区及被轰炸区域的儿童说的话》的文章,希望“把接近战地以及有被轰炸危险的城市或村镇中的儿童儘量收集,尽力把他们移送较为安全的地带”,“最好能教养他们,使其在抗战岁月中,身心仍得良善发育,为国家製造一些未来的良善有用的国民,使他们成为我们复兴的一批台柱子”(《新民族》周刊1938年11月22日第2卷第18期)。1942年,她曾购买近千元床桌罩等手工艺品,寄往美国,请胡适帮忙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内地战时儿童保育院。凌叔华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儿童倾注了爱心,也寄予了厚望。在《中国儿女》这部小说中,她借建国、徐廉、宛英等几个“中国儿女”,表达了自己抗战救亡的爱国热情,同时把复兴国家的希望放在他们这些未来的“台柱子”身上。
《阿昭》原载《燕大月刊》1928年1月12日第1卷第4期,目录页署名凌叔华女士,内页标题下署名叔华,文末说明是“录1924年旧作”。凌叔华的小说多以女性和儿童为主角,这篇小说则运用儿童视角,集中“回忆”了“我童年最感兴味的一个人”,一个厨师,一个“三十来岁”的男性。这在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中也可算是“另类”。《阿昭》是凌叔华的一篇逸文,在已经出版的各种作品集中都未见收录。
凌叔华既是作家,也是画家。总体来看,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情节比较单一,结构比较单纯,具有一种“写意画”的特点。正如朱光潜所说的:“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论自然画与人物画——凌叔华作〈小哥儿俩〉序》,《天下周刊》1946年5月5日创刊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中的作品,除个别文字(如“的”等)和标点依据现行用法酌予改动外,其余皆一仍其旧;本书是我和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先生合作编订的;感谢凌叔华研究专家陈学勇先生,我们在选定篇目时曾得到他的热情指导和帮助。
陈建军
2009年12月2日于珞珈山麓
序言
热爱母语,亲近经典
整整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儿童读物,孙毓修先生的童话集《无猫国》在上海出版。从此,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徐徐拉开……
啊,百年中国!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内忧外患;多少风起云涌,多少崎岖艰辛;多少欢欣,又多少痛苦;多少阴晴,又多少冷暖……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百年来儿童文学历程的史诗长卷。它也向我们呈现着一个无限光明和美丽的母语世界,一片无限丰富和绚丽的文学原野。
文学家果戈理曾经说过:“你将永远诧异于俄国语言的珍贵,它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件馈赠,都似大颗闪光的珍珠。”是的,只有对那些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母语,而且了解她们到“入骨”的程度,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她们的美丽的人,我们的文学,才会真正地展示出它们全部的美质与知性,以及它们全部的丰富与神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就是这样一套品种繁富、风格斑斓的书系。
徜徉在这套百年长卷里,我相信,每一位读者,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都不能不对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母语顿生无限的景仰感和膜拜感。美丽的汉语,不仅仅是我们赖依生存和交往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我们全部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它还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语言与回忆之乡,是我们这个古老、智慧而苦难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谱系,甚至是我们全部的记忆与命运!
对于这样一套百年长卷,仅仅用“阅读”二字来对待是不够的。不,我们也许应该溯流而上,重新居住和生活在它的字里行间。无论是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寓言……它们都曾经是20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孩子童年时代最美好的阅读记忆。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学世界,中国四代儿童文学作家和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在其中生活、探索、呼吸和成长。
通往一座座儿童文学高峰的路径有千万条,但每一段路途上都付出过艰辛,每一段路途上都留下了果实。正如梅子涵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海洋。很远的日子在下面,昨天的故事在水上。离开童年,童年反而加倍情深,每条小鱼的游动都是感情的尾巴在摇,情深处没有不美好的风光”。
当然,时间和文学的选择法则,也都是严格和无情的。历史的目光,读者的心灵,最终所淘汰和扬弃的,也只是那些迎风媚俗的诗歌、童话、小说和散文,而另有一些作品,却经受住了一次次严格的检验和磨洗而流传了下来,并且被打上了优秀或杰作的标识,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不同的作家因为年代、地域、文化背景以及性格气质、个人知识谱系的不同,所写出的每一部作品也会在题材、形式、想像力、感情状态、文字风格等等方面而各有千秋。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不难感到,任何时代背景下的作家,在努力传达着各自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广泛地赢得了当时的那一代小读者的同时,也都在力图扩大自己的感受範围,拓展自己的创作视野,甚至为自己的作品设定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世界性标準”。他们都在努力地为“一切的孩子”写作,为未来的孩子写作,为整个人类,为全世界的孩子而写作。
因此,从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那些伟大和温暖的,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的童话精神和文学精神,那些天真的和具有童年趣味的儿童精神,那种舔犊般的母爱情感,那种对于每一个弱小生命个体的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呵护,那种纯真、仁慈、宽容、细腻与柔和的情感,以及对儿童本位的坚持,对儿童游戏精神和幽默品质的寻找,等等。
是的,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代作家,都在认真地维护着和守望着、努力地传承着和延续着在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早期儿童文学家那里就已经拥有的,那种对于童心的尊重、关怀和维护的“童话传统”。
回眸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沧桑,我们还会看到,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所走过的世纪之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春花秋月、山重水複。漫漫长路上,留下了众多的拓荒者、垦植者、播种者、泅渡者、乃至殉道者的艰辛、歌哭、梦想和收穫……历史曾让那些人经历了那幺多的崎岖和弯道,付出了那幺多的心血和艰难,但是翻开这套长卷,我们会看到,他们私下的亲密的传承关係,却是多幺美好!
所有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在内,如果不是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土壤里直接生长出来,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我们从这套书系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也有我们的儿童文学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繫在一起的苦难之歌、艰辛之歌、欢乐之歌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之歌。它们将在我们美丽的母语里,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里,飞翔、传播,直至永恆。
徐鲁
2009年12月24日
整整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儿童读物,孙毓修先生的童话集《无猫国》在上海出版。从此,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徐徐拉开……
啊,百年中国!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内忧外患;多少风起云涌,多少崎岖艰辛;多少欢欣,又多少痛苦;多少阴晴,又多少冷暖……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百年来儿童文学历程的史诗长卷。它也向我们呈现着一个无限光明和美丽的母语世界,一片无限丰富和绚丽的文学原野。
文学家果戈理曾经说过:“你将永远诧异于俄国语言的珍贵,它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件馈赠,都似大颗闪光的珍珠。”是的,只有对那些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母语,而且了解她们到“入骨”的程度,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她们的美丽的人,我们的文学,才会真正地展示出它们全部的美质与知性,以及它们全部的丰富与神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就是这样一套品种繁富、风格斑斓的书系。
徜徉在这套百年长卷里,我相信,每一位读者,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都不能不对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母语顿生无限的景仰感和膜拜感。美丽的汉语,不仅仅是我们赖依生存和交往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我们全部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它还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语言与回忆之乡,是我们这个古老、智慧而苦难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谱系,甚至是我们全部的记忆与命运!
对于这样一套百年长卷,仅仅用“阅读”二字来对待是不够的。不,我们也许应该溯流而上,重新居住和生活在它的字里行间。无论是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寓言……它们都曾经是20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孩子童年时代最美好的阅读记忆。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学世界,中国四代儿童文学作家和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在其中生活、探索、呼吸和成长。
通往一座座儿童文学高峰的路径有千万条,但每一段路途上都付出过艰辛,每一段路途上都留下了果实。正如梅子涵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海洋。很远的日子在下面,昨天的故事在水上。离开童年,童年反而加倍情深,每条小鱼的游动都是感情的尾巴在摇,情深处没有不美好的风光”。
当然,时间和文学的选择法则,也都是严格和无情的。历史的目光,读者的心灵,最终所淘汰和扬弃的,也只是那些迎风媚俗的诗歌、童话、小说和散文,而另有一些作品,却经受住了一次次严格的检验和磨洗而流传了下来,并且被打上了优秀或杰作的标识,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不同的作家因为年代、地域、文化背景以及性格气质、个人知识谱系的不同,所写出的每一部作品也会在题材、形式、想像力、感情状态、文字风格等等方面而各有千秋。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不难感到,任何时代背景下的作家,在努力传达着各自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广泛地赢得了当时的那一代小读者的同时,也都在力图扩大自己的感受範围,拓展自己的创作视野,甚至为自己的作品设定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世界性标準”。他们都在努力地为“一切的孩子”写作,为未来的孩子写作,为整个人类,为全世界的孩子而写作。
因此,从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那些伟大和温暖的,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的童话精神和文学精神,那些天真的和具有童年趣味的儿童精神,那种舔犊般的母爱情感,那种对于每一个弱小生命个体的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呵护,那种纯真、仁慈、宽容、细腻与柔和的情感,以及对儿童本位的坚持,对儿童游戏精神和幽默品质的寻找,等等。
是的,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代作家,都在认真地维护着和守望着、努力地传承着和延续着在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早期儿童文学家那里就已经拥有的,那种对于童心的尊重、关怀和维护的“童话传统”。
回眸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沧桑,我们还会看到,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所走过的世纪之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春花秋月、山重水複。漫漫长路上,留下了众多的拓荒者、垦植者、播种者、泅渡者、乃至殉道者的艰辛、歌哭、梦想和收穫……历史曾让那些人经历了那幺多的崎岖和弯道,付出了那幺多的心血和艰难,但是翻开这套长卷,我们会看到,他们私下的亲密的传承关係,却是多幺美好!
所有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在内,如果不是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土壤里直接生长出来,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我们从这套书系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也有我们的儿童文学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繫在一起的苦难之歌、艰辛之歌、欢乐之歌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之歌。它们将在我们美丽的母语里,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里,飞翔、传播,直至永恆。
徐鲁
2009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