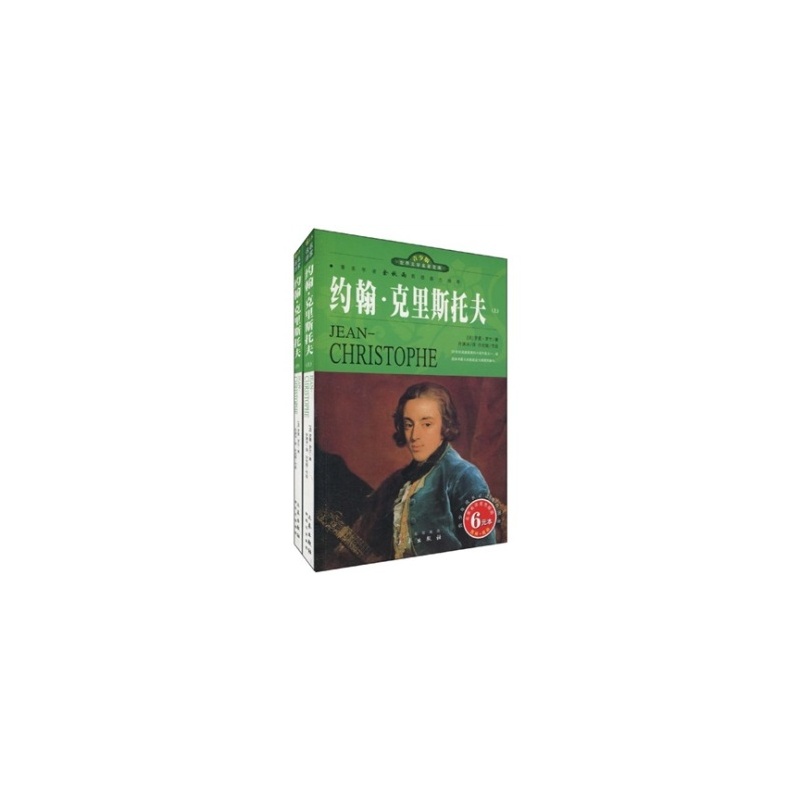该书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它叙说了一个真诚的音乐家是如何反抗虚伪轻浮的社会,从而在与社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升华自己、完善自己;它描述了一颗坚强刚毅的心是如何战胜自己心灵深处的怯懦卑鄙的阴暗面,由幼稚走向成熟。它又是一部音乐的史诗,作者用他对音乐精神的深刻理解,描述了病态堕落的艺术与健康奋进的音乐之间的斗争,歌颂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音乐理念……
基本介绍
- 书名:世界文学文库041:约翰•克里斯托夫
- 作者: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 页数:1149页
- 开本:32
- 品牌:北京天下智慧
- 外文名:Jean Christophe
- 译者:许渊沖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9787540212452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十年积思,十年命笔,小说逐捲髮表时,已誉满全欧,罗曼·罗兰藉此于一九一五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浩瀚的篇章,恢宏的蕴涵,使这部长篇超越主人公个人的历险记,而成为人类的一部伟大史诗。
浩瀚的篇章,恢宏的蕴涵,使这部长篇超越主人公个人的历险记,而成为人类的一部伟大史诗。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年1月29日-1944年12月30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8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範学校,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其后入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当研究生。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範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
罗曼·罗兰早期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共称《名人传》。同时发表了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着名的人道主义作家。
两次大战之间,罗曼·罗兰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潮,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悦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着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罗曼·罗兰早期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共称《名人传》。同时发表了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着名的人道主义作家。
两次大战之间,罗曼·罗兰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潮,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悦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着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媒体推荐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着名翻译家 傅雷
20世纪的最高贵的小说作品。
——英国作家 爱德蒙·高斯
——着名翻译家 傅雷
20世纪的最高贵的小说作品。
——英国作家 爱德蒙·高斯
图书目录
《文学文库041:约翰·克里斯托夫(上册)》目录:
第一卷黎明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卷清晨
第一部约翰·米歇尔之死
第二部奥托
第三部蜜娜
第三卷青春
第一部于莱之家
第二部莎冰
第三部阿达
第四卷反抗
第一部流沙
第二部失落
第三部解脱
作者和影子的对话
第五卷市场
第一部
第二部
《文学文库041:约翰·克里斯托夫(下册)》目录:
第六卷安东妮蒂
第七卷楼中
第一部
第二部
第八卷女友
第九卷燃荆
第一部
第二部
第十卷新生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别了约翰·克里斯托夫
后序
后记
第一卷黎明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卷清晨
第一部约翰·米歇尔之死
第二部奥托
第三部蜜娜
第三卷青春
第一部于莱之家
第二部莎冰
第三部阿达
第四卷反抗
第一部流沙
第二部失落
第三部解脱
作者和影子的对话
第五卷市场
第一部
第二部
《文学文库041:约翰·克里斯托夫(下册)》目录:
第六卷安东妮蒂
第七卷楼中
第一部
第二部
第八卷女友
第九卷燃荆
第一部
第二部
第十卷新生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别了约翰·克里斯托夫
后序
后记
后记
六十年前,我读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欣喜若狂;六十年后,我读许渊沖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喜出望外。克利斯朵夫是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夫是我的新朋友。温故知新,心心相印。傅雷生于一九○八年,比我大十岁;许渊沖生于一九二一年,比我小三岁。我和许渊沖是西南联大同学,他在外文系,我在数学系。当年我们发黑如漆,风华正茂;如今我们白髮苍苍,饱经沧桑。我们都到了所谓耄耋之年。可喜的是我们都有一颗年轻不老的赤子之心。我读过他写的《追忆逝水年华》和《诗书人生》,写得很精彩,我很喜欢。
傅雷的全译本出版于一九四六年。傅雷时年三十八岁。我至今还保存着上海骆驼书店出版的一九四八年的版本。许渊沖的译本出版于二○○○年。他已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为什幺《约翰·克里斯托夫》有这幺大的魅力,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热爱真理的人们的朋友?罗曼·罗兰在此书的后序中说:“友爱是这部作品的源头活水,从绝望中却流出了英雄主义精神的长江大河。”“我把这本不是不朽的书献给一切不是不朽的人,书中的呼声要说的是:‘兄弟们,互相亲近吧,忘记我们的分歧,思考我们不得不共同对付的苦难吧!我们之间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可怜的人;而我们惟一持久的幸福是互相了解,以便达到互爱的目的:智慧和爱,这是在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两个无底深渊之间,能淹没黑夜的惟一光明。’”“《约翰·克里斯托夫》永远是新生一代的战友。《克里斯托夫》一直是‘全世界英勇斗争、受苦受难取得胜利的自由男女’的兄弟。”
罗大冈在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八O年版的译本序言中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根本的、总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无可怀疑的现实主义价值,主要就在于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手段表现了这种战斗的人道主义。”“战斗的人道主义,是罗曼·罗兰全部作品的灵魂,也是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灵魂。”他又说:“译者傅雷的谨严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对于这部世界名着在我国的流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大冈是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翻译家。罗曼·罗兰的另一部巨着《母与子》就是他译的。罗大冈的序言中说:“罗曼·罗兰(1866-1944)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罗曼·罗兰用十年时间(1903-1912)创造了里程碑式的巨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获得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家。
为什幺许渊冲要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呢?他在译者序言中说:“我认为重译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一个好方法。我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二十一世纪的翻译家应该和作家不分高下,所以我要和傅雷展开竞赛。”“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仅为了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首先是译者‘自得其乐’。”“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比美而不逊色,如果再创造的‘美’有幸能够胜过傅译,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如果‘自得其乐’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不是最高级的‘善’,最大的好事吗?乐趣有人共享就会倍增,无人同赏却会消失。这就是我重译这部皇皇巨着的原因。”
我喜欢许渊沖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这是一部形神兼备、青出于蓝的好译本。
通过比较,我个人可以得出结论:许渊沖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比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好。
这一点也不奇怪。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许渊沖敢和傅雷竞赛,他心中有数,稳操胜券。傅雷的译本译于三四十年代,当时直译之风甚盛,傅雷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许渊沖的译本译于九十年代,许渊沖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就学问、修养、人生阅历来说,许渊沖占了优势。从傅译到许译,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汉语在发展,文学翻译也在发展。因此,在语言文字、翻译技巧方面,许渊沖也占了优势。更何况许渊沖还有一套继承前人、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和六十年文学翻译的丰富经验。
有人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飞跃.许渊沖的“发挥译语优势”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飞跃。傅雷和许渊沖对文学翻译的贡献功不可没。
许渊沖在他的《诗书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第四三八页和四一三页上说:傅雷在一九五一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强调:“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傅雷提出过两条翻译原则:一是神似重于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内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时,往往出现妙译;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时,往往出现败笔。后来我重译他译过的作品,就学其长而避其短了。”
许渊沖的这段话指出了傅雷译文的长处和短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页上说:“朱光潜先生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翻译的成熟境界。”在第四三九、四四O页上又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不能分割的,‘不逾矩’是低标準,‘从心所欲’是高标準。”“关于‘矩’或‘度’的问题,我想用画家吴冠中的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风筝不断线’,飞得越高越好。‘线’就是‘矩’或‘度’。”他在第三七七页上说:“朱先生的《谈美》和《诗论》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吴冠中说得好:‘我们是朱先生的奶餵大的。’” 关于“发挥译语优势”和“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四O、四四一、四六五、四六六页上说:“我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是根据我六十年来翻译了四十本文学作品总结出来的论点。”“一般说来,原作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但是原作最好的文字,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译文;原作最好的次序,更不能变成对等的译文次序,因此,中外互译的时候,无论文字还是次序,有时可以对等,有时不能对等;如不对等,多是原文占优势,译文占劣势,那就需要展开竞赛,发挥译语优势,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如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就是取得优势了。”“翻译要能使人好之,甚至乐之,就需要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要儘量利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西方科学派提出‘对等’、‘等值’、‘等效’、形似直译的译论。公式是:1+1=2。中国艺术学派提出意译、神似、发挥译语优势的理论,也就是说,译者可以译出原文内容所有,原文形式所无的词语。公式是:1+1>2。”
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六五页上说:我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十个字:“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所谓“美”,就是把鲁迅的文字“三美”论套用于文学翻译;所谓“化”,就是把钱钟书的“化镜”说分解为深化、等化、浅化“三-化”论;所谓“之”,就是把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总结为“三之”论;所谓艺术,就是把朱光潜的艺术论套用于文学翻译,认为文学翻译和文学译论都是艺术。总起来说.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的艺术。所谓“创”,就是把郭沫若的“文学翻译等于创作”提高为再创论;所谓“优”,就是发挥译语优势论;所谓“似”,就是傅雷的神似说;所谓竞赛,即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论。合起来说,“美”和“优”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化”和“创”是方法论;“之”和“似”是目的论;艺术和竞赛是认识论。
关于“三美”、“三化”、“三之”、“三似”,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三七五、三七六、三七五、三九一、四四六、四四七、三九六页上说:“‘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用英文来说,就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指具有意美、音美的文字,best order指具有形美和音美的次序。”“‘意美、音美、形美’就是和‘神似,统一的‘意似、音似、形似’,就是译诗时不可忘的‘精’;而可忘的‘粗’是和‘神似,矛盾的‘意似、音似、形似’。”“‘意似’是译诗的低标準,‘意美’是高标準,‘三美,是最高标準。‘意似’只能使读者‘知之’,‘意美’却能使读者‘好之’,‘三美’才能使读者‘乐之’。这是我译诗的‘三美’理论。”“翻译要求‘意似’,不求‘形似’,最妙的是‘神似’。”“妙译来自得意忘形。”“文学翻译是化原文为译文的艺术,是化原文之美为译文之美的艺术,用的方法,我看主要是等化、浅化、深化三种。“‘三化,是要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发挥优势。”“我在《三似新论》中提出了形似、意似、神似的公式,分别是1+12。”
讲得很全面,深入浅出,有继承,也有创新。有些论点,如“发挥优势”、“三似”公式。在杨振宁的科学理论中找到了依据。(《诗书人生》第396页)这说明文理是相通的。杨振宁读了许渊沖的《追忆逝水年华》英译稿后,说“很精彩”,并写了英文序言。英文本Vanished Springs由美国纽约Vantage Press于一九九八年出版。(《诗书人哇》第398、451页)许渊沖把他的文学翻译理论概括为“美化之艺术”五个字,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十个字。概括得好,总结得好。中国人太聪明了,中文也太妙了!用五个字和十个字就能把全套理论言简意赅地概而括之,总而结之。这五个字,这十个字,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啊!
许渊沖的文学翻译理论是“美化之艺术”,许渊沖的文学翻译是“美化之翻译”。
许渊沖的文学翻译理论很好,但很难做到。“妙译来自得意忘形”,讲得很好,但很难掌握分寸。“得意忘形”,不能“忘乎所以”。直译(形似)比较容易,意译(意似)就比较难,妙译(神似)就很难了。要做到“妙译”,必须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很高的外文水平,很强的驾驭中文的能力。由“巧译”而得“妙译”,功夫全在一个“巧”字上。这个“巧”字,是“巧夺天工”的“巧”,不是“弄巧成拙”的“巧”。
译诗难,译中国古诗词更难。许渊沖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Songs of the Immortals)被英国最负盛名的企鹅出版公司收入《企鹅丛书》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他的译本能在国际大出版社企鹅图书公司出版,并且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全世界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本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好评,说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令人讚赏钦佩。许渊沖为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许渊沖说:“我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诗书人生》第381、374、435、33、16页)
早在一九七六年,钱钟书看了许渊沖英译《毛泽东诗词》后回信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这些话,即是鼓励,又是鞭策。(《诗书人生》第111、112页)
许渊沖说:“我认为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译论,因为它能解决世界上最难的中西互译问题,但中国人受压迫太久,自卑心理太重,所以我要像杨振宁说的那样提高民族自尊心,把翻译提高到创作的地位,建立中国学派的译论。”(《诗书人生》第450页)
许渊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他辛勤耕耘,硕果纍纍。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他的许多译作和文章都是六十岁以后译出来和写出来的。
抗战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西南联大校友中,成就最大、贡献最大的是杨振宁。杨振宁扬名天下,与日月同辉,天上就有一颗杨振宁星。杨振宁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最杰出的代表。王浩是数学系最杰出的代表。汪曾祺是中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外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原来是查良铮(穆旦),可惜他死得太早。现在许渊沖超过了他。许渊沖和杨振宁一样,也必将扬名天下。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他们是西南联大校友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
许光锐
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南京龙江小区芳草园
傅雷的全译本出版于一九四六年。傅雷时年三十八岁。我至今还保存着上海骆驼书店出版的一九四八年的版本。许渊沖的译本出版于二○○○年。他已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为什幺《约翰·克里斯托夫》有这幺大的魅力,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热爱真理的人们的朋友?罗曼·罗兰在此书的后序中说:“友爱是这部作品的源头活水,从绝望中却流出了英雄主义精神的长江大河。”“我把这本不是不朽的书献给一切不是不朽的人,书中的呼声要说的是:‘兄弟们,互相亲近吧,忘记我们的分歧,思考我们不得不共同对付的苦难吧!我们之间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可怜的人;而我们惟一持久的幸福是互相了解,以便达到互爱的目的:智慧和爱,这是在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两个无底深渊之间,能淹没黑夜的惟一光明。’”“《约翰·克里斯托夫》永远是新生一代的战友。《克里斯托夫》一直是‘全世界英勇斗争、受苦受难取得胜利的自由男女’的兄弟。”
罗大冈在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八O年版的译本序言中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根本的、总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无可怀疑的现实主义价值,主要就在于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手段表现了这种战斗的人道主义。”“战斗的人道主义,是罗曼·罗兰全部作品的灵魂,也是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灵魂。”他又说:“译者傅雷的谨严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对于这部世界名着在我国的流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大冈是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翻译家。罗曼·罗兰的另一部巨着《母与子》就是他译的。罗大冈的序言中说:“罗曼·罗兰(1866-1944)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罗曼·罗兰用十年时间(1903-1912)创造了里程碑式的巨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获得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家。
为什幺许渊冲要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呢?他在译者序言中说:“我认为重译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一个好方法。我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二十一世纪的翻译家应该和作家不分高下,所以我要和傅雷展开竞赛。”“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仅为了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首先是译者‘自得其乐’。”“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比美而不逊色,如果再创造的‘美’有幸能够胜过傅译,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如果‘自得其乐’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不是最高级的‘善’,最大的好事吗?乐趣有人共享就会倍增,无人同赏却会消失。这就是我重译这部皇皇巨着的原因。”
我喜欢许渊沖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这是一部形神兼备、青出于蓝的好译本。
通过比较,我个人可以得出结论:许渊沖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比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好。
这一点也不奇怪。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许渊沖敢和傅雷竞赛,他心中有数,稳操胜券。傅雷的译本译于三四十年代,当时直译之风甚盛,傅雷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许渊沖的译本译于九十年代,许渊沖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就学问、修养、人生阅历来说,许渊沖占了优势。从傅译到许译,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汉语在发展,文学翻译也在发展。因此,在语言文字、翻译技巧方面,许渊沖也占了优势。更何况许渊沖还有一套继承前人、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和六十年文学翻译的丰富经验。
有人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飞跃.许渊沖的“发挥译语优势”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飞跃。傅雷和许渊沖对文学翻译的贡献功不可没。
许渊沖在他的《诗书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第四三八页和四一三页上说:傅雷在一九五一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强调:“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傅雷提出过两条翻译原则:一是神似重于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内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时,往往出现妙译;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时,往往出现败笔。后来我重译他译过的作品,就学其长而避其短了。”
许渊沖的这段话指出了傅雷译文的长处和短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页上说:“朱光潜先生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翻译的成熟境界。”在第四三九、四四O页上又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不能分割的,‘不逾矩’是低标準,‘从心所欲’是高标準。”“关于‘矩’或‘度’的问题,我想用画家吴冠中的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风筝不断线’,飞得越高越好。‘线’就是‘矩’或‘度’。”他在第三七七页上说:“朱先生的《谈美》和《诗论》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吴冠中说得好:‘我们是朱先生的奶餵大的。’” 关于“发挥译语优势”和“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四O、四四一、四六五、四六六页上说:“我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是根据我六十年来翻译了四十本文学作品总结出来的论点。”“一般说来,原作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但是原作最好的文字,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译文;原作最好的次序,更不能变成对等的译文次序,因此,中外互译的时候,无论文字还是次序,有时可以对等,有时不能对等;如不对等,多是原文占优势,译文占劣势,那就需要展开竞赛,发挥译语优势,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如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就是取得优势了。”“翻译要能使人好之,甚至乐之,就需要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要儘量利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西方科学派提出‘对等’、‘等值’、‘等效’、形似直译的译论。公式是:1+1=2。中国艺术学派提出意译、神似、发挥译语优势的理论,也就是说,译者可以译出原文内容所有,原文形式所无的词语。公式是:1+1>2。”
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六五页上说:我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十个字:“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所谓“美”,就是把鲁迅的文字“三美”论套用于文学翻译;所谓“化”,就是把钱钟书的“化镜”说分解为深化、等化、浅化“三-化”论;所谓“之”,就是把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总结为“三之”论;所谓艺术,就是把朱光潜的艺术论套用于文学翻译,认为文学翻译和文学译论都是艺术。总起来说.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的艺术。所谓“创”,就是把郭沫若的“文学翻译等于创作”提高为再创论;所谓“优”,就是发挥译语优势论;所谓“似”,就是傅雷的神似说;所谓竞赛,即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论。合起来说,“美”和“优”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化”和“创”是方法论;“之”和“似”是目的论;艺术和竞赛是认识论。
关于“三美”、“三化”、“三之”、“三似”,许渊沖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三七五、三七六、三七五、三九一、四四六、四四七、三九六页上说:“‘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用英文来说,就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指具有意美、音美的文字,best order指具有形美和音美的次序。”“‘意美、音美、形美’就是和‘神似,统一的‘意似、音似、形似’,就是译诗时不可忘的‘精’;而可忘的‘粗’是和‘神似,矛盾的‘意似、音似、形似’。”“‘意似’是译诗的低标準,‘意美’是高标準,‘三美,是最高标準。‘意似’只能使读者‘知之’,‘意美’却能使读者‘好之’,‘三美’才能使读者‘乐之’。这是我译诗的‘三美’理论。”“翻译要求‘意似’,不求‘形似’,最妙的是‘神似’。”“妙译来自得意忘形。”“文学翻译是化原文为译文的艺术,是化原文之美为译文之美的艺术,用的方法,我看主要是等化、浅化、深化三种。“‘三化,是要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发挥优势。”“我在《三似新论》中提出了形似、意似、神似的公式,分别是1+12。”
讲得很全面,深入浅出,有继承,也有创新。有些论点,如“发挥优势”、“三似”公式。在杨振宁的科学理论中找到了依据。(《诗书人生》第396页)这说明文理是相通的。杨振宁读了许渊沖的《追忆逝水年华》英译稿后,说“很精彩”,并写了英文序言。英文本Vanished Springs由美国纽约Vantage Press于一九九八年出版。(《诗书人哇》第398、451页)许渊沖把他的文学翻译理论概括为“美化之艺术”五个字,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十个字。概括得好,总结得好。中国人太聪明了,中文也太妙了!用五个字和十个字就能把全套理论言简意赅地概而括之,总而结之。这五个字,这十个字,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啊!
许渊沖的文学翻译理论是“美化之艺术”,许渊沖的文学翻译是“美化之翻译”。
许渊沖的文学翻译理论很好,但很难做到。“妙译来自得意忘形”,讲得很好,但很难掌握分寸。“得意忘形”,不能“忘乎所以”。直译(形似)比较容易,意译(意似)就比较难,妙译(神似)就很难了。要做到“妙译”,必须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很高的外文水平,很强的驾驭中文的能力。由“巧译”而得“妙译”,功夫全在一个“巧”字上。这个“巧”字,是“巧夺天工”的“巧”,不是“弄巧成拙”的“巧”。
译诗难,译中国古诗词更难。许渊沖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Songs of the Immortals)被英国最负盛名的企鹅出版公司收入《企鹅丛书》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他的译本能在国际大出版社企鹅图书公司出版,并且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全世界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本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好评,说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令人讚赏钦佩。许渊沖为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许渊沖说:“我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诗书人生》第381、374、435、33、16页)
早在一九七六年,钱钟书看了许渊沖英译《毛泽东诗词》后回信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这些话,即是鼓励,又是鞭策。(《诗书人生》第111、112页)
许渊沖说:“我认为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译论,因为它能解决世界上最难的中西互译问题,但中国人受压迫太久,自卑心理太重,所以我要像杨振宁说的那样提高民族自尊心,把翻译提高到创作的地位,建立中国学派的译论。”(《诗书人生》第450页)
许渊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他辛勤耕耘,硕果纍纍。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他的许多译作和文章都是六十岁以后译出来和写出来的。
抗战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西南联大校友中,成就最大、贡献最大的是杨振宁。杨振宁扬名天下,与日月同辉,天上就有一颗杨振宁星。杨振宁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最杰出的代表。王浩是数学系最杰出的代表。汪曾祺是中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外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原来是查良铮(穆旦),可惜他死得太早。现在许渊沖超过了他。许渊沖和杨振宁一样,也必将扬名天下。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他们是西南联大校友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
许光锐
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南京龙江小区芳草园
序言
译序(节选)
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名着中,最能引起一代人共鸣的,可能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早在五十年代,这本书就是北京大学出借率最高的一部。到了六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部小说中的个人奋斗精神。
一九三二年,罗曼·罗兰对一个德国的採访记者说过:“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法国人,但是我从来就对本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从小时候起,我吸收的营养来自法国的高乃依和莫里哀,德国的席勒和贝多芬,英国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俄国的托尔斯泰。我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矛盾上(不管是时代的还是国家的冲突),而是深入内心,发现无论在哪里,人心都是一样的。”
关于“永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五卷第二部中说过:爱和恨,取和舍的意志,人的一切力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就接近“永恆”了,就已经成了“永恆”的一部分。每个人身上都有“永恆”的因素。……各种矛盾都溶化在永恆的“力”之中。对克里斯托夫说来,重要的是唤醒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的“永恆之力”,把木柴投入“永恆”的火炉之中,使“永恆”燃烧得更加光辉灿烂。这就是克里斯托夫,罗曼·罗兰,贝多芬如何超越痛苦,寻求幸福的。《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但是以贝多芬为蓝本,而且还有罗曼·罗兰自己生活的蹤迹。他在第六卷《安东妮蒂》第一页描写他的故乡:使他们和乡土难分难解的,是一种说不出,除不掉的共同感,无论粗俗文雅,人人都感到几百年来,和土地同生活,共呼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自己也成了一块泥土……死气沉沉的小小古城在一条运河一动不动的浑水中照着自己闷闷不乐的面容,周围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耕过的土地,草场,小溪,树林,然后又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这种没有动静的景象,这种和谐的沉闷,这种单调,对他说来却有一种魅力,一片深刻的温情,他自己也不明白,甚至不以为贵,但却一往情深,终生难忘。
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我们看到了一片心灵的海洋。《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一句,傅雷译成“江声浩蕩,自屋后上升。”有人说是译文胜过了原文,有人却说声音不能浩蕩,我看如果说“江流滚滚,声震屋后。”也就可以算是译笔生花了。贝多芬说过:“为了更好,没有一条清规戒律不可打破的。”原文也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文本。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王尔德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父母,不是思想的产儿。”新世纪语言学革新派更认为语言不但表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我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就合理地表现了语言的创造意义。
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名着中,最能引起一代人共鸣的,可能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早在五十年代,这本书就是北京大学出借率最高的一部。到了六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部小说中的个人奋斗精神。
一九三二年,罗曼·罗兰对一个德国的採访记者说过:“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法国人,但是我从来就对本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从小时候起,我吸收的营养来自法国的高乃依和莫里哀,德国的席勒和贝多芬,英国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俄国的托尔斯泰。我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矛盾上(不管是时代的还是国家的冲突),而是深入内心,发现无论在哪里,人心都是一样的。”
关于“永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五卷第二部中说过:爱和恨,取和舍的意志,人的一切力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就接近“永恆”了,就已经成了“永恆”的一部分。每个人身上都有“永恆”的因素。……各种矛盾都溶化在永恆的“力”之中。对克里斯托夫说来,重要的是唤醒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的“永恆之力”,把木柴投入“永恆”的火炉之中,使“永恆”燃烧得更加光辉灿烂。这就是克里斯托夫,罗曼·罗兰,贝多芬如何超越痛苦,寻求幸福的。《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但是以贝多芬为蓝本,而且还有罗曼·罗兰自己生活的蹤迹。他在第六卷《安东妮蒂》第一页描写他的故乡:使他们和乡土难分难解的,是一种说不出,除不掉的共同感,无论粗俗文雅,人人都感到几百年来,和土地同生活,共呼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自己也成了一块泥土……死气沉沉的小小古城在一条运河一动不动的浑水中照着自己闷闷不乐的面容,周围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耕过的土地,草场,小溪,树林,然后又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这种没有动静的景象,这种和谐的沉闷,这种单调,对他说来却有一种魅力,一片深刻的温情,他自己也不明白,甚至不以为贵,但却一往情深,终生难忘。
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我们看到了一片心灵的海洋。《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一句,傅雷译成“江声浩蕩,自屋后上升。”有人说是译文胜过了原文,有人却说声音不能浩蕩,我看如果说“江流滚滚,声震屋后。”也就可以算是译笔生花了。贝多芬说过:“为了更好,没有一条清规戒律不可打破的。”原文也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文本。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王尔德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父母,不是思想的产儿。”新世纪语言学革新派更认为语言不但表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我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就合理地表现了语言的创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