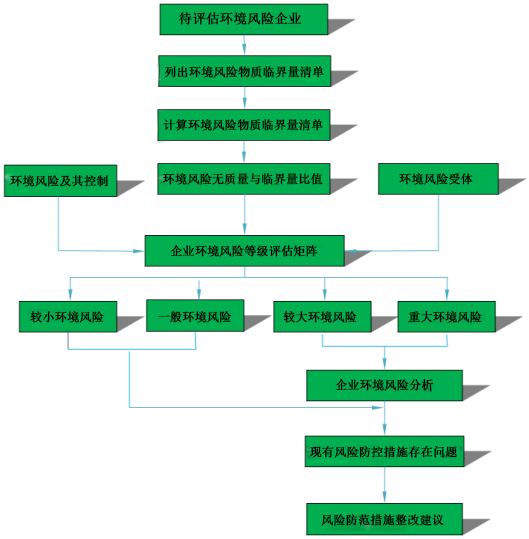环境风险管理是我国“十二五”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突发性事故的环境风险影响,也包含低浓度有毒有害物质长期排放累积效应的风险,而后者也是目前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累积性环境风险涉及环境科学、环境化学、生态学、毒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是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方面,也是环境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基础。
基本介绍
- 中文名:累积性风险评估
- 外文名:Cumulative risk assessment
- 国外:美国开始最早
- 国内:尚无明确定义
- 程式:三个阶段
- 食品:食品中化学物质的累积暴露
累积性风险评估研究背景
环境风险管理是我国“十二五”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突发性事故的环境风险影响,也包含低浓度有毒有害物质长期排放累积效应的风险,而后者也是目前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累积性环境风险涉及环境科学、环境化学、生态学、毒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是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方面,也是环境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基础。
美国是最早开始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研究的国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将累积风险(cumulativerisk)定义为来源于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多个压力源的综合暴露的组合风险,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则是分析、表征和量化那些由于多种原因及来自多个压力源的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危害,其特徵体现为多来源、多暴露方式、多传播途径、多影响、持续时间长、人口集中的组合风险的综合评估。按照该定义,USEPA的累积性风险主要指组合风险和叠加风险,其涵盖宽泛,是综合风险评估。
国内对累积性环境风险尚未明确定义,也缺乏对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流程与内容的技术指导。目前开展的研究主要考虑人类健康和生态两方面,侧重于单一污染物或化学品进入环境后潜在的健康危害和生态效应。王炳权等认为累积性环境风险指自然及人类活动中潜在的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危害的行为,主要强调风险源的潜在累积影响。也有学者将蓝藻水华归为累积性环境风险的研究範畴。笔者通过梳理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重点从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发展历史、评价流程、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实践案例等进行阐述,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展望,以期为进一步开展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研究提供参考。
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发展历史
20世纪70年代,美国首先提出了累积效应的概念,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则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1989年,美国超级基金会首次提出了环境风险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1996年,美国颁布了《食品质量保护法(FQPA)》,提出为保护儿童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农药残留的标準,引入“综合风险”(来自多个压力源)、“累积暴露”(具有相同毒性机制农药)的概念,并要求USEPA开展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研究,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开始正式发展起来。1997年,USEPA提出了“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指南第一部分:规划和範围”,阐明了累积性环境风险的评估重点由单个压力源、单一传播途径、单一评估端点转向多来源、多传播途径、多评估受体的评估,从而为风险管理者提供一个清晰、透明、合理的评估基础。1998年,USEPA首次提出了农药的共同毒性作用机制,并于1999年颁布了该类农药的识别方法,经多次修订,于2002年正式颁布具有相同毒性作用机制的农药物质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指导档案,提出了进行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原则和对该类物质评估的10步评估程式,首次将不确定性因素作为风险评估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在此基础上,2002年,USEPA对39种有机磷农药开始了初步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2003年,USEPA颁布了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框架,对框架的3个主要阶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旨在确定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过程中的基本元素,这是USEPA在长期努力下制定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指南的第一步,是处理累积性环境风险和风险决策关係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004年,国际环境司法委员会(EnvironmentJustice)研讨了环境司法决策和累积性风险关係,指出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在风险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风险评估也转向以社区为基础,考虑人类、动物、植物及生态系统的综合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2010年,K.Sexton等提出应更多地将风险决策和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联繫起来,并从公众健康的角度探讨了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在风险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向着更全面、更科学、更人性的方向发展。儘管在科学理论方面,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实践上却相对落后,缺乏可用来支持理论分析的具体实践方法和工具。为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USEPA开发了一个关于污染场地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工具,提供了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应用程式线上访问工具箱。随着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研究的不断发展,USEPA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档案(图1),包括相关的评估指南、政策和特定的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方法等,为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欧洲也逐渐重视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研究,欧盟第六框架计画(FP6)将多压力源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新方法(NoMiracle)作为重要研究项目之一,自2004年起,来自17个欧盟成员国的100余位科学家参加了该项目,研究了化学、生物和物理等综合风险源作用下的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包括难降解化学物质的累积性环境风险,低剂量有毒物质的长期累积效应,对特殊人群尤其是儿童的健康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等。
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程式
开展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3个主要阶段可概括如下:(1)规划、审定和问题构建阶段。在该阶段,风险管理者、风险评估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团队首先确定评估对象的来源、目标、範围、深度、关注点和方法,形成资料库,进而构建一个概念模型和一个分析计画。(2)风险分析阶段。该阶段主要是专家套用风险评估方法开展工作的过程,包括形成暴露的途径、考虑压力源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受体的脆弱性分析,开展风险的识别、剂量效应分析、用定性或者定量的方法进行暴露评估等。(3)风险表征阶段。即对风险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表述,对风险水平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得出危害最大、优先考虑的风险源,预测评估人口或亚种群的风险。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明确不确定性的来源和可能造成的额外风险,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方法与套用
食品中化学物质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于1993年首次提出食品中化学物质的累积暴露概念。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在1997年强调,应重视具有共同毒性作用机制的化学品的联合暴露问题。此后,英国食品标準局(FSA)、荷兰健康委员会、USEPA和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等机构先后提出了食品中化学物质(如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化学污染物)的累积暴露风险评估方法,为制定新的、更加科学的化学物质限量标準提供了科学手段。1996年,美国的《食品质量保护法(FQPA)》正式出台,旨在保障农产品安全、保护儿童权益和解决法律体系的不一致性问题。食品农药残留研究主要包括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两方面。A.F.Jensen等、以具有共同毒性机制的农药为风险源,研究了丹麦饮食中摄入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农药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基于1996—2001年的监测数据,评估了35种有机磷农药和氨基甲酸酯农药的环境风险,结果表明,该地区并没有暴露在有机磷农药和氨基甲酸酯农药的长期累积性风险中。2002年,USEPA华盛顿办公室发布了具有共同毒性机理的农药化学物质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指南,并详细提出了对于杀虫剂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10个步骤,用剂量效应分析和相对效能因子法来量化其累积性环境风险。同年,USEPA按照FQPA的要求首次开展了食品中有机磷农药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并于2005年公布了灭多威、甲萘威、克百威、抗蚜威等11种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结果。P.E.Boon等基于2003—2005年对荷兰人群和1~6岁儿童饮食中的农药残余量的数据统计,採用了乙醯甲胺磷和氨基乙二醯指数等效因子法来量化风险源,开展了对苹果、香蕉、白菜、萝蔔等食用农产品中26种有机磷和8种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对于儿童,只有少部分有机磷农药残余超过了健康标準。2006年11月EFSA组织农药暴露评估和毒理学方面的专家召开了农药累积性暴露评估研讨会,对具有相同作用机制的农药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所需要的数据来源和方法论进行了广泛讨论,在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的需求和重要意义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在目前人类进行农药残留暴露和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中,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具有优先性,但方法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2012年,S.C.Wason等整合化学和非化学压力源对农药暴露进行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套用已有的生理学的药代动力学模型(PBPKPD模型)研究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儿童暴露在有机磷农药和其他农药的累积性环境风险,分析表明,化学和非化学因素都会影响有机磷农药的暴露,对于一个给定剂量有机磷农药值,通过不同压力源的组合累积性环境风险可变性高达5倍。
环境中污染物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
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首先要识别风险来源,由于多种风险源及其在不同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和风险特徵不同,因此,多风险源的识别与表征是评估的重点。M.Holmstrup等研究并总结了化学品风险源与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包括环境中重金属类(镉、铜、汞、铅、锌、镍)、农药类(阿特拉津、毒死蜱、敌百虫、对硫磷等)、多环芳烃类、表面活性剂类风险源在高温、低温、乾旱缺水、溶解氧减少、病菌存在等条件下的生态毒性效应,其在不同研究条件下表现为协同促进效应、反效应、无作用效应及免疫效应。研究表明,开展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应将极端的自然条件要素作为考虑因素。1999年,USEPA农药项目组(OPP)启动了一项美国地质勘探(USGS)工程,旨在通过依据现有监测点位获得的数据来评估饮用水水源处24种有机磷农药污染物残留的分布。美国地质勘探局第一次尝试用回归方程的方法来预测服务6000万人饮用水的567条河流中的总氮,其数据和输出结果可以用在基于全国範围内暴露人口上的评估,并且可识别出值得特别关注的区域,这种方法对由监测数据推断其地表水中农药残留浓度的研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2008年,S.Shrestha等充分利用统计、空间和水文等资源以及多元回归模型,计算了日本富士河流域有机物、营养物的输出係数,结果表明,大多数污染物输出係数回归效果显着,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利用土地类别解释了超过85%的负荷变化的现象,并提出了需进一步调查的水质监测站的数量、採样频率和採样时间,从而提高方法的稳定性和实用性,这些结果可用于确定合适的实践管理以改善流域水体质量。2012年,B.D.Crawford等构建了一个评估模型,将累积性环境风险用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来统一度量,并且协调癌症和非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利用半定量化方法评估了假定的饮用水中50种化学品组成的複杂混合物的风险,得出了複杂混合物的累积性环境风险由其中几种主要的组分所主导的结论。A.M.J.Ragas等套用DALYs方法评估了城市环境中苯、甲苯、萘和几种典型农药的累积性环境风险。饮用水消毒副产物(DBPs)可以通过人的口腔、皮肤被人体吸收,一些流行病学和毒理学研究表明,生殖、发育影响和癌症与含氯饮用水相关。2013年,L.K.Teuschler等将暴露模型和药物代谢动力学模型组合发展了一种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新方法———累积相对效能因子法(CRPF),并且评估了13种主要DBPs3个暴露途径下的剂量效应和不同行为模式的影响。该方法遵循了剂量叠加和反应叠加原则,可以为不同种类的DBPs混合物导致的累积性环境风险提供更为科学的评估。此外,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也可用于评价突发环境事件急性暴露后对健康的长期效应,K.M.Wollin等研究了德国北部一起环氧氯丙烷泄漏污染事故后人群暴露的长期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周边居民暴露浓度较低,致癌风险极低。
国内开展的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研究
国内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研究工作主要是从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两方面进行的。在生态风险评价方面,吴健等阐述了累积效应、流域累积效应和累积效应评估的概念,并从技术、哲学和社会价值体系三方面着重论述了累积效应评估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流域累积效应评估的研究和展望,提出了更加完善合理的流域生态管理思路。许妍等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对流域生态风险评价进行了概念界定与特徵分析,按照风险源、生态受体、生态终点的分类标準对流域生态风险评价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尝试构建反映流域时空尺度变化规律的生态风险评价概念模型。冯承莲等对中国主要河流中多环芳烃(PAHs)生态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价,结合毒性资料库对蒽、芘、苯并[a]蒽、苯并[a]芘等7种PAHs进行了机率风险分析,并得到了它们的风险大小排序。刘卫国等对博斯腾湖流域进行生态风险评价,採用遥感技术确定生态风险受体,通过生态风险的综合计算和GIS分析叠加,得到博斯腾湖区域综合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卢宏玮等以洞庭湖地区东、南、西三部分为研究区域,根据其特殊的背景,将工业源、农业源作为其污染类风险源,对洞庭湖流域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建立了由氮毒性污染指数、磷毒性污染指数、重金属类毒性污染指数共同组成的毒性污染指数,并与自然灾害指数和系统本身的生态指数构成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计算了洞庭湖流域的综合生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