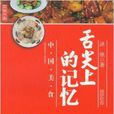《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是洪烛将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描述的一部新风格的美食书,点评了北京、南京、杭州、扬州、苏州、广东、山西、湖北、湖南、河南、云南、东北等各地的饮食文化特徵,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
基本介绍
- 书名: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
- 类型:烹饪美食与酒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7516600474, 9787516600474
- 作者:洪烛
-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 页数:242页
- 开本:16
- 品牌:新华出版社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编辑推荐: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係,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还有历史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故乡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作者简介
洪烛,原名王军,1967年生于南京,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出版长篇小说《两栖人》,诗集《南方音乐》、《你是一张旧照片》,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浪漫的骑士》、《梦游者的地图》、《抚摸古典中国》、《北京的金粉遗事》等。
图书目录
业余美食家(自序)
一、祖先餐桌上的记忆
中国人的吃
酒池肉林
儒家的吃
隐士的吃
不散的筵席
清宫的吃
食无鱼
鱼图腾
文化味素
素斋
二、“食”间的过往
豆腐
药膳:“中国范儿”的经典
夜雨剪春韭
竹 笋
饮食与时间
南有年糕,北有饺子
火锅的褒贬
茶乾引起的想像
甜蜜蜜的莲子汤
“海底东坡肉”:海参
“春不老”:长年菜
吃豆芽像吃利息
火腿与状元
童年的饥饿
坚硬的稀粥
螃蟹与田螺的故事
烹饪中的“混血儿”:乱炖
以想像力为调料:凤爪
从青蚕豆到茴香豆
北京大白菜
青苔可食
中国的粽子
成肉:味觉的纪念
三、地图上的饮食
北京的吃(一)
北京的吃(二)
北京的吃(三)
老字号不老
文人与北京小吃
草原上的酒歌
西安的吃
浑厚朴实的山西吃食
武昌鱼
南京人的味蕾
秦淮小吃
去周庄吃鱼
醋酸绽放的镇江
杭州的美味传说
勾魂的苏州小吃
扬州的吃
云南的食智慧
楚雄的味道
游吃长治
平遥牛肉及其他
海宁的吃
在南通吃河豚
长江下游的鱼
一、祖先餐桌上的记忆
中国人的吃
酒池肉林
儒家的吃
隐士的吃
不散的筵席
清宫的吃
食无鱼
鱼图腾
文化味素
素斋
二、“食”间的过往
豆腐
药膳:“中国范儿”的经典
夜雨剪春韭
竹 笋
饮食与时间
南有年糕,北有饺子
火锅的褒贬
茶乾引起的想像
甜蜜蜜的莲子汤
“海底东坡肉”:海参
“春不老”:长年菜
吃豆芽像吃利息
火腿与状元
童年的饥饿
坚硬的稀粥
螃蟹与田螺的故事
烹饪中的“混血儿”:乱炖
以想像力为调料:凤爪
从青蚕豆到茴香豆
北京大白菜
青苔可食
中国的粽子
成肉:味觉的纪念
三、地图上的饮食
北京的吃(一)
北京的吃(二)
北京的吃(三)
老字号不老
文人与北京小吃
草原上的酒歌
西安的吃
浑厚朴实的山西吃食
武昌鱼
南京人的味蕾
秦淮小吃
去周庄吃鱼
醋酸绽放的镇江
杭州的美味传说
勾魂的苏州小吃
扬州的吃
云南的食智慧
楚雄的味道
游吃长治
平遥牛肉及其他
海宁的吃
在南通吃河豚
长江下游的鱼
序言
经常在大小媒体发表一些谈论饮食文化的文字,便有人将我称做美食家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当美食家可比当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愉快多了),另一方面又很惶恐:不敢当,不敢当,在下纯粹是业余的……这倒不是说,我对美食的鉴赏能力,尚且处于业余水平;而是觉得什幺事情,一旦变成专业的,就没劲了。想想自己以前的道路吧:作为文学青年(业余作者),胸怀梦想、豪情万丈,每一根神经都是敏锐而兴奋的,跟全天候搜寻的雷达似的,即使跟路人借个火儿,也会触发灵感,赶紧找个本子记下;后来如愿以偿地成为专业作家,这位书商请客吃饭,明天参加那家杂誌的笔会,反而变得麻木了,强打起精神应付四处的约稿,可气弱时写文章,也跟炒菜似的,动作稍慢点就炒煳了。可见,即使是文学,一旦变成职业,也会使人产生“审美疲劳”(正如邂逅的美女一旦娶进家里,就离黄脸婆不远了)。
所以我只承认是饮食文化的票友,而不去做那所谓的专家。是啊,做个置身于边缘的爱好者就足够刺激。我相信,真正的酒鬼做不成浅尝辄止的品酒师,他会忘乎所以地一饮而尽;同样,充满理性的品酒师绝不是真正的酒鬼,其舌头再灵验,也不过是一小件精密的仪器。况且,若强调谁谁是专业的美食家(美食家有专业的吗?),那等于说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嘛!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以遍尝天下美味为能事、为乐事,很奢侈的。早先,八旗子弟之流这幺乾过。
几乎大多数美食家都是业余的。至少,在心理上是业余的。创业守业之余,把品尝美食作为一大嗜好,作为享受生活的辅助手段。并不见得真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钻研、当成一项生意来经营。美食家虽带着一个“家”字,却算不上一种头衔或职称。顶多代表一种闲适、放鬆的人生态度。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见过职业化的美食家。譬如某些不太正规的烹饪协会、餐饮协会的头头脑脑,四处筹办什幺评奖呀、大赛呀,倒也搞得色、香、味俱全,弄得星级饭店老闆们待之如贵宾、如“首长”。但我总怀疑:这一类美食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把餐饮业搞得跟官场似的,打着美食家的幌子,谋求名利。其实,真正的美食乃至美食家,还是在民间啊!
我还是做我的散兵游勇,隐于市井,在偏僻的地域和不知名的餐馆间搜寻,那些让人终生难忘的滋味。既不骗吃又不骗喝,顶多是真正被打动了,写点文字,“骗”点儿稿费。足以用来润笔兼润筷子了。
我住美术馆一带时,常去对面胡同里的悦宾菜馆小酌,模仿鲁迅住绍兴会馆时夜饮于广和居的风度。“悦宾”是北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个体餐馆,做的菜有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我是熟客,可老闆并不知道我是个作家。我们纯粹是君子之交,或布衣之交。我写《北京的梦影星尘》一书,其中有一篇《寻找北京菜》,专门提到“悦宾”,此文又被《北京青年报》等不少报刊转载。确实给“悦宾”锦上添花了。譬如,出版人杨葵告诉我,他请刚从上海来的美女作家赵波吃饭,赵波恰巧刚买了我的书,点名要杨葵领她去“洪烛写到的悦宾菜馆”。还有一次,我在家中接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潘的电话,她当时主持《读书时间》节目,读书时读到我写“悦宾”的文章,一时兴起,就开车赶过来“一识庐山真面目”。她说已在“悦宾”点好菜了,问我是否有空陪她聊聊。瞧,我快成“三陪”了。朋友们一去“悦宾”,就会想到马路对面住着洪烛,就会约我过去一起坐坐。直到我搬家好几年后,偶尔还能接到类似的电话。受我影响而知道“悦宾”的这班京城男女文人,有的又为“悦宾”写过新的文章,譬如古清生的《北京:深藏不露的美食中心》:“去那里是诗人洪烛领引的,酒家看上去是一户人家,掀开门帘才发现别有洞天。我在‘悦宾’吃过地道的北京菜。据洪烛说,许多当红歌星都开着车来此处品饮……”
再去“悦宾”,老闆从柜檯里取出本书,说是一位慕名赶来的食客留给他的。他说最近老有新客人拿着本《北京的梦影星尘》来吃饭,他翻看到作者照片,才知道是我写的。老闆很感谢,那顿饭一定要免单。其实,我都已经拿到书的版税了,还在乎这顿饭钱嘛。但老闆的心意我还是领了。我也挺感谢“悦宾”的,不仅帮助我领略到老北京的滋味,还提供了一个好素材。
李潘跟我一样,忘不掉北京的悦宾菜馆了。如果她同样忘不掉在“悦宾”的第一顿饭,是跟谁一起吃的,就更好了。(开个玩笑!)她后来做一期美食节目,又想到“悦宾”了,又想到我了。特意让摄製组请我去现场解说。我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正宗的北京菜或老北京菜,不会出现在五星级的王府饭店里,而是隐藏在这不起眼儿的胡同深处,只要胡同还在、四合院还在,老北京的滋味就不会失传……
这些年,我边走边唱、边吃边写,倒是积累下一大堆美食散文。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开了《不散的筵席》专栏,在《深圳特区报》开了《闲话美食》专栏,在《南京日报》开了《洪烛谈吃》专栏,还在香港《大公报》、《齐鲁晚报》、《大河报》、《扬子晚报》等诸多报刊成系列地发表。部分旧作早先曾结集为《中国人的吃》,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又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着作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的评论:“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像力……”正如日文版易名为《中国美味礼讚》,我是以讚美的态度来对待美食的。讚美故乡的美食,讚美异乡的美食,讚美祖国的美食,讚美属于全人类的美食。
这幺看来,我对弘扬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还是做了点小事情的。至少,我还是对得起那些感动过我的食物的,包括製造这些食物的人。
我要为美食写一首零碎而又完整的讚美诗。这是否属于一种理想?
可以说,只要生命不息,对美食的激情就不会削减,这首漫长的讚美诗就会伴随一日三餐而延续下去。
我不是第一个这幺做的,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写的是美食的故事,我与美食的故事,以及我与一些同样热爱美食的人的故事。姑且作为精神会餐的菜谱吧。我仍然觉得自己只算一个美食爱好者。顶多占了点会舞文弄墨的便宜。但不管是鉴赏食物,还是舞文弄墨,跟李渔、袁枚、周作人、梁实秋等一系列前辈相比,我都差得远呢!他们才是我心目中的美食家。
在这两方面,我都曾经拜汪曾祺先生为师。虽然并未举办什幺正式的拜师仪式。1992年,湖北的《芳草》杂誌约我给汪老写一篇印象记,我就前往北京城南的汪宅,和他海阔天空聊了一个下午。一开始是谈文学,后来话题就转移了;因为彼此是江苏老乡,就议论起南方的饮食及其与北京风味的比较。汪曾祺让我领略到他的大雅,乃至大俗;而在他身上,大雅就是大俗,大俗就是大雅。他喜欢在家中烹饪,觉得跟做文章一样刺激,讲究起承转合,讲究绘声绘色,讲究画龙点睛。这就是所谓的性格:一个人的烹调手段,跟他的写作方法息息相通。汪曾祺说自己的性格,受了老师沈从文不少的影响。而我,则受了汪曾祺的影响。我原本写诗的,自从和汪老成为忘年交之后,改写散文了。一下子就从诗化的人生转人散文化的人生。从海市蜃楼里走出来,亲近人间烟火。那段时间,经常去汪宅求教,有幸品尝到主人按江南风格烹製的菜餚,总唤起心头丝丝缕缕的乡愁,恰似烟波江上的点点帆影。
汪曾祺先生已不在了。可他送我的几册书中的美食散文,却经常翻读。脑海里总出现这样的画面:老人慢腾腾地把一碟碟小炒,从厨房里端到客厅的圆桌上,笑眯眯地招手——“请坐吧!”真正是曲终人不散。嘿,一想起汪曾祺,我哪敢自称为美食家啊,我哪敢自称为美食散文家啊?给这位文学“大厨子”打下手的资格,都不知道够不够。
我只能勉强算作业余美食家,还有一个羞于启齿的原因:自己尚且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虽然跑遍全中国、品尝过无数的美味,但吃完后用心去学进而会做的,没有几道。我真有古君子之风:动口而不动手。当然,我也动手的,只不过动的是手中的笔,再无余力去掌勺了。
偶尔炒几道家常菜,仅供自己玩儿。不敢请客。怕露怯、献丑。但对业余时间写的美食散文,倒不藏着掖着,并不畏惧再挑剔的读者。
我有一条歪理:美食家,并不见得热爱下厨房,只要喜欢下馆子就可以。厨师手再勤,不过是食物的奴隶,而美食家动动嘴皮子(会吃且会说),依然是食物的主人。指点江山的人,不需要上火线拼刺刀。
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华医药》节目,连续做几期春节食谱,邀我去主讲。我有言在先:我可不擅长从营养学的角度去剖析,要谈也谈的是这些食物跟传统文化的关係,甚至用文化来“解构”这些食物,说到底就是侃,侃晕了算!不管是把观念侃晕了,还是把自己侃晕了。主持人洪涛很惊喜,说正需要这种新风格。我就逐一评点、演绎了豆腐、竹笋、年糕、饺子、火锅等传统食品,越侃越带劲。洪涛那天没来得及吃早点,听了我的描述,既饿且馋,表情无比生动且灿烂,夸我提供了一顿精神大餐。我差点儿跟她开玩笑:你才是秀色可餐呢!
拍摄的时间太长,过了午饭的时间。收机器的间歇,摄像师议论:听洪老师谈最后一道菜——螃蟹炒年糕,正是肚子饿的时候,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馋得差点儿晕过去。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评价”。
写这本书,我也抱着如此的态度:侃,侃晕了算!
馋嘴的读者,意志力稍微薄弱点儿的读者,最好备上两片“晕车灵”哟!
马上,咱们就要出发了。一趟美食之旅,一趟文化之旅,一趟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之旅。
所以我只承认是饮食文化的票友,而不去做那所谓的专家。是啊,做个置身于边缘的爱好者就足够刺激。我相信,真正的酒鬼做不成浅尝辄止的品酒师,他会忘乎所以地一饮而尽;同样,充满理性的品酒师绝不是真正的酒鬼,其舌头再灵验,也不过是一小件精密的仪器。况且,若强调谁谁是专业的美食家(美食家有专业的吗?),那等于说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嘛!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以遍尝天下美味为能事、为乐事,很奢侈的。早先,八旗子弟之流这幺乾过。
几乎大多数美食家都是业余的。至少,在心理上是业余的。创业守业之余,把品尝美食作为一大嗜好,作为享受生活的辅助手段。并不见得真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钻研、当成一项生意来经营。美食家虽带着一个“家”字,却算不上一种头衔或职称。顶多代表一种闲适、放鬆的人生态度。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见过职业化的美食家。譬如某些不太正规的烹饪协会、餐饮协会的头头脑脑,四处筹办什幺评奖呀、大赛呀,倒也搞得色、香、味俱全,弄得星级饭店老闆们待之如贵宾、如“首长”。但我总怀疑:这一类美食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把餐饮业搞得跟官场似的,打着美食家的幌子,谋求名利。其实,真正的美食乃至美食家,还是在民间啊!
我还是做我的散兵游勇,隐于市井,在偏僻的地域和不知名的餐馆间搜寻,那些让人终生难忘的滋味。既不骗吃又不骗喝,顶多是真正被打动了,写点文字,“骗”点儿稿费。足以用来润笔兼润筷子了。
我住美术馆一带时,常去对面胡同里的悦宾菜馆小酌,模仿鲁迅住绍兴会馆时夜饮于广和居的风度。“悦宾”是北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个体餐馆,做的菜有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我是熟客,可老闆并不知道我是个作家。我们纯粹是君子之交,或布衣之交。我写《北京的梦影星尘》一书,其中有一篇《寻找北京菜》,专门提到“悦宾”,此文又被《北京青年报》等不少报刊转载。确实给“悦宾”锦上添花了。譬如,出版人杨葵告诉我,他请刚从上海来的美女作家赵波吃饭,赵波恰巧刚买了我的书,点名要杨葵领她去“洪烛写到的悦宾菜馆”。还有一次,我在家中接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潘的电话,她当时主持《读书时间》节目,读书时读到我写“悦宾”的文章,一时兴起,就开车赶过来“一识庐山真面目”。她说已在“悦宾”点好菜了,问我是否有空陪她聊聊。瞧,我快成“三陪”了。朋友们一去“悦宾”,就会想到马路对面住着洪烛,就会约我过去一起坐坐。直到我搬家好几年后,偶尔还能接到类似的电话。受我影响而知道“悦宾”的这班京城男女文人,有的又为“悦宾”写过新的文章,譬如古清生的《北京:深藏不露的美食中心》:“去那里是诗人洪烛领引的,酒家看上去是一户人家,掀开门帘才发现别有洞天。我在‘悦宾’吃过地道的北京菜。据洪烛说,许多当红歌星都开着车来此处品饮……”
再去“悦宾”,老闆从柜檯里取出本书,说是一位慕名赶来的食客留给他的。他说最近老有新客人拿着本《北京的梦影星尘》来吃饭,他翻看到作者照片,才知道是我写的。老闆很感谢,那顿饭一定要免单。其实,我都已经拿到书的版税了,还在乎这顿饭钱嘛。但老闆的心意我还是领了。我也挺感谢“悦宾”的,不仅帮助我领略到老北京的滋味,还提供了一个好素材。
李潘跟我一样,忘不掉北京的悦宾菜馆了。如果她同样忘不掉在“悦宾”的第一顿饭,是跟谁一起吃的,就更好了。(开个玩笑!)她后来做一期美食节目,又想到“悦宾”了,又想到我了。特意让摄製组请我去现场解说。我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正宗的北京菜或老北京菜,不会出现在五星级的王府饭店里,而是隐藏在这不起眼儿的胡同深处,只要胡同还在、四合院还在,老北京的滋味就不会失传……
这些年,我边走边唱、边吃边写,倒是积累下一大堆美食散文。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开了《不散的筵席》专栏,在《深圳特区报》开了《闲话美食》专栏,在《南京日报》开了《洪烛谈吃》专栏,还在香港《大公报》、《齐鲁晚报》、《大河报》、《扬子晚报》等诸多报刊成系列地发表。部分旧作早先曾结集为《中国人的吃》,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又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着作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的评论:“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像力……”正如日文版易名为《中国美味礼讚》,我是以讚美的态度来对待美食的。讚美故乡的美食,讚美异乡的美食,讚美祖国的美食,讚美属于全人类的美食。
这幺看来,我对弘扬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还是做了点小事情的。至少,我还是对得起那些感动过我的食物的,包括製造这些食物的人。
我要为美食写一首零碎而又完整的讚美诗。这是否属于一种理想?
可以说,只要生命不息,对美食的激情就不会削减,这首漫长的讚美诗就会伴随一日三餐而延续下去。
我不是第一个这幺做的,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写的是美食的故事,我与美食的故事,以及我与一些同样热爱美食的人的故事。姑且作为精神会餐的菜谱吧。我仍然觉得自己只算一个美食爱好者。顶多占了点会舞文弄墨的便宜。但不管是鉴赏食物,还是舞文弄墨,跟李渔、袁枚、周作人、梁实秋等一系列前辈相比,我都差得远呢!他们才是我心目中的美食家。
在这两方面,我都曾经拜汪曾祺先生为师。虽然并未举办什幺正式的拜师仪式。1992年,湖北的《芳草》杂誌约我给汪老写一篇印象记,我就前往北京城南的汪宅,和他海阔天空聊了一个下午。一开始是谈文学,后来话题就转移了;因为彼此是江苏老乡,就议论起南方的饮食及其与北京风味的比较。汪曾祺让我领略到他的大雅,乃至大俗;而在他身上,大雅就是大俗,大俗就是大雅。他喜欢在家中烹饪,觉得跟做文章一样刺激,讲究起承转合,讲究绘声绘色,讲究画龙点睛。这就是所谓的性格:一个人的烹调手段,跟他的写作方法息息相通。汪曾祺说自己的性格,受了老师沈从文不少的影响。而我,则受了汪曾祺的影响。我原本写诗的,自从和汪老成为忘年交之后,改写散文了。一下子就从诗化的人生转人散文化的人生。从海市蜃楼里走出来,亲近人间烟火。那段时间,经常去汪宅求教,有幸品尝到主人按江南风格烹製的菜餚,总唤起心头丝丝缕缕的乡愁,恰似烟波江上的点点帆影。
汪曾祺先生已不在了。可他送我的几册书中的美食散文,却经常翻读。脑海里总出现这样的画面:老人慢腾腾地把一碟碟小炒,从厨房里端到客厅的圆桌上,笑眯眯地招手——“请坐吧!”真正是曲终人不散。嘿,一想起汪曾祺,我哪敢自称为美食家啊,我哪敢自称为美食散文家啊?给这位文学“大厨子”打下手的资格,都不知道够不够。
我只能勉强算作业余美食家,还有一个羞于启齿的原因:自己尚且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虽然跑遍全中国、品尝过无数的美味,但吃完后用心去学进而会做的,没有几道。我真有古君子之风:动口而不动手。当然,我也动手的,只不过动的是手中的笔,再无余力去掌勺了。
偶尔炒几道家常菜,仅供自己玩儿。不敢请客。怕露怯、献丑。但对业余时间写的美食散文,倒不藏着掖着,并不畏惧再挑剔的读者。
我有一条歪理:美食家,并不见得热爱下厨房,只要喜欢下馆子就可以。厨师手再勤,不过是食物的奴隶,而美食家动动嘴皮子(会吃且会说),依然是食物的主人。指点江山的人,不需要上火线拼刺刀。
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华医药》节目,连续做几期春节食谱,邀我去主讲。我有言在先:我可不擅长从营养学的角度去剖析,要谈也谈的是这些食物跟传统文化的关係,甚至用文化来“解构”这些食物,说到底就是侃,侃晕了算!不管是把观念侃晕了,还是把自己侃晕了。主持人洪涛很惊喜,说正需要这种新风格。我就逐一评点、演绎了豆腐、竹笋、年糕、饺子、火锅等传统食品,越侃越带劲。洪涛那天没来得及吃早点,听了我的描述,既饿且馋,表情无比生动且灿烂,夸我提供了一顿精神大餐。我差点儿跟她开玩笑:你才是秀色可餐呢!
拍摄的时间太长,过了午饭的时间。收机器的间歇,摄像师议论:听洪老师谈最后一道菜——螃蟹炒年糕,正是肚子饿的时候,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馋得差点儿晕过去。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评价”。
写这本书,我也抱着如此的态度:侃,侃晕了算!
馋嘴的读者,意志力稍微薄弱点儿的读者,最好备上两片“晕车灵”哟!
马上,咱们就要出发了。一趟美食之旅,一趟文化之旅,一趟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