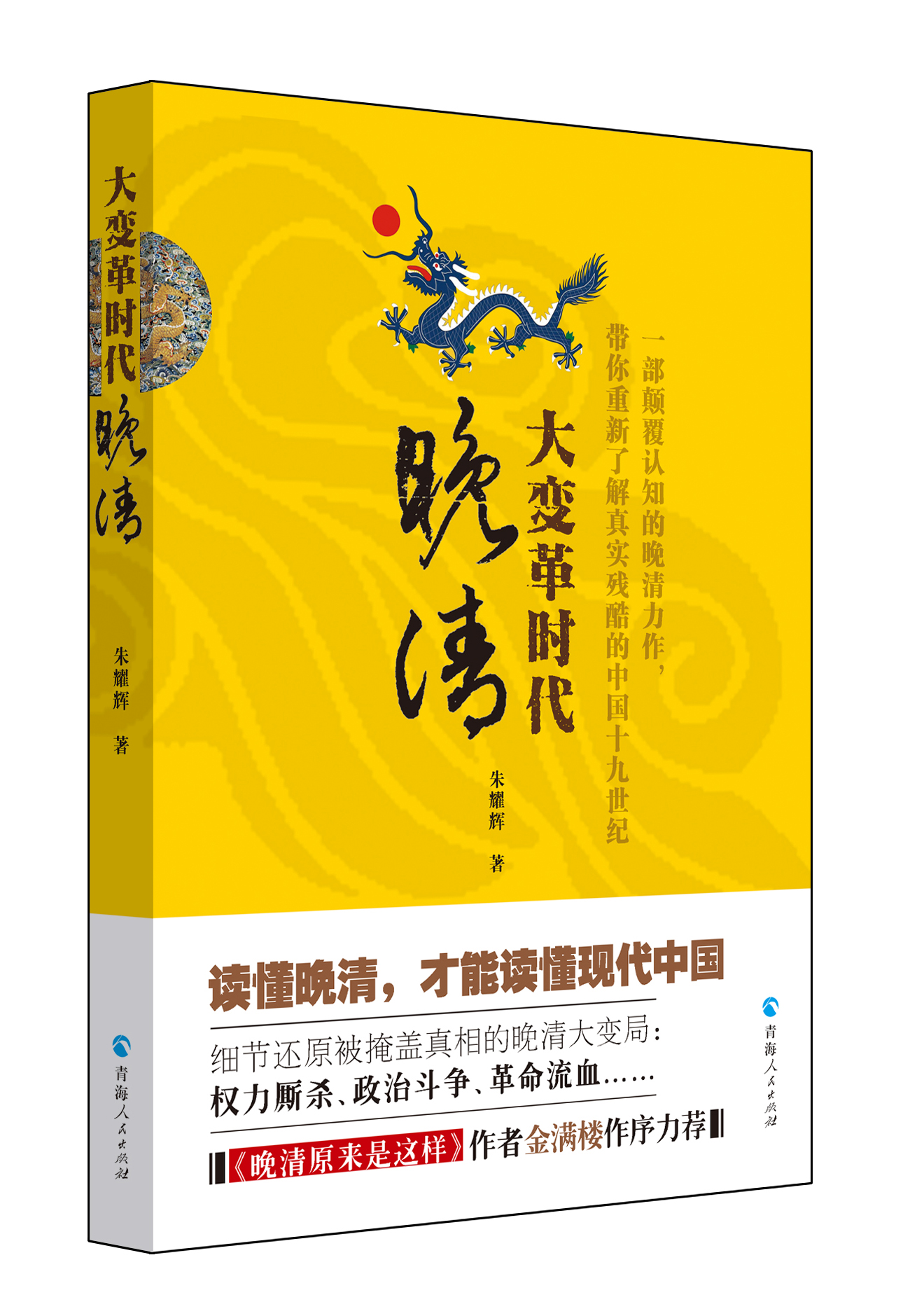《大变革时代:晚清》2018年1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朱耀辉。该书讲述了自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近一个多世纪的晚清历史。
基本介绍
- 书名:大变革时代:晚清
- 作者:朱耀辉
- ISBN:9787225054407
- 页数:315页
- 定价:¥39.00
-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 装帧:平装
- 开本: 24 x 17.2 x 1.6 cm
基本信息
大变革时代:晚清
书 名 大变革时代:晚清
作 者 朱耀辉
类 别 历史
页 数 315页
定 价 39.00元
ISBN 9877225054407
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1
装 帧 平装
开 本 16开
纸 张 胶版纸
版 次 1
字 数 25万
内容简介
《大变革时代:晚清》2018年1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朱耀辉。该书讲述了自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近一个多世纪的晚清历史。翻开本书,告诉您晚清是如何一步步失控并走向覆亡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朱耀辉,笔名浪子,着名自媒体人,天涯论坛知名写手,90后新锐历史作家。青海省互助县人,求学京城,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现任职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自幼喜好文史,博览群书,学富思博,拥有深厚的国学和史学功底,诗词作品曾获省级荣誉和奖励。负登天之志,乏兰台之才,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完成多部作品,欲以文学之法,书写千年历史,并载笔者思道。

作品目录
第一章:马戛尔尼访华:两个文明的冲突
在天朝上国的闭关政策面前,马嘠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返回伦敦。然而这次旅行也让使团看清了清朝盛世下的荒芜,如同捅破一层窗户纸,打破了传教士在欧洲建立的东方神话。
第二章:鸦片战争:这一次,我们挨打了
沉浸在春梦之中的道光皇帝,自以为凭着自己的勤俭节约便可以实现太平盛世,然而区区几千人的英国军队,便把一个拥有四万万民众的中国打得颜面扫地,迷梦从此醒来,近代化的道路就在这样的炮火中开始了。
第三章:天父下凡:洪秀全的天国之梦
天京之变,君臣内讧,兄弟相残,石达开走了,偌大的天京城内空空蕩蕩。多年后,军中流传着一首歌谣: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当长工。
第四章:洋务运动:传统王朝的“洋跃进”
鸦片战争后,“康乾盛世”已经成为爱新觉罗王朝的一个回忆,吏治腐败、财政枯竭、外交疲软,改革势在必行,先行者们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改革道路,他们能成功幺?
第五章:甲午国殇:四千年大梦之觉醒
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命运。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群议汹汹,李鸿章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第六章:戊戌变法:知识分子的救国幻想
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康梁书生气太浓,做事太过强硬,不懂得妥协,短短百日就想把几千年的制度翻过来,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这又怎幺可能做得到?头颅滚动,漫天血雨中,知识分子的救国幻想也由此幻灭。
第七章:庚子国变:民众的非理性排外运动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1900年的那个夏天,义和拳涌入北京城,外交官危在旦夕,清王朝命悬一线,伴随着愚昧、迷信、狂暴与杀戮,终于闯下了滔天大祸。谁该为这场民众的非理性暴动买单?
第八章: 清末新政:一场失控的系统性改革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的威权和尊严几乎蕩然无存。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时局,清廷启动了第三轮也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新政改革,开始由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逐步转型。在此过程中,士绅阶层逐渐崛起,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力量,与清政府渐行渐远。
第九章: 辛亥革命:一个王朝的隐退
武昌城的一声枪响,震撼着整箇中国大地。剎那间,革命烽火蔓延全国,十八行省纷纷宣布独立。埋葬了封建腐朽的旧王朝,能否迎来一个新生的充满朝气的民国?历史三峡,虽暗流险礁,可国人终究挂帆起行。
创作背景
写完这部稿子,我重温了一遍《走向共和》。
历史是什幺?
英国诗人雪莱说,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迴旋诗。高晓松说,历史是精子,牺牲亿万,才有一个活到今天。
读中国近代史,有人愤怒,有人伤感,有人遗憾,还有人无奈。作为读者,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评判历史,喜欢或厌恶,这都没有错。但作为着史者来说,重要的是在千般感慨、万端思绪之上的理性分析,你要对你的读者负责,对笔下的人物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
为什幺要写晚清史?
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 晚清开始的。当然,与一般的着史者不同,我把这个开始的节点往前调了一下,在我的历史框架中,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这场大变革,起自1793年,迄于1911年,百余年间,不知多少人头落地,汇成滔滔血海。
我们这个民族,背负了太多沉重的历史,沉重到一个转身是如此艰难。晚清七十年的历史,留给后人的不只是有形的耻辱,还有巨大的心灵创伤。我们忘不了圆明园的沖天大火,也忘不了八国联军的肆意蹂躏,这是晚清历史上对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的两次伤害,当然还有后来的南京大屠杀。这创伤如此之深,以至于到今天都无法完全癒合。
在我看来,一部晚清史,始终在追寻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曾创造了领先世界的灿烂文明,但却在近代历史的潮流中,落伍了。然而,我们无法苛责前辈,作为今人,应该充分尊重前人的历史选择。儘管他们受眼界和知识的限制,无法打破这个铁屋子,但至少他们没有甘于沉沦,而是在绝境中艰难前行,探索未来的道路,儘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忽然想到李鸿章那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100多年前的历史,离我们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多年来,由于文科教育的失败,我们的历史枯燥乏味,远谈不上什幺历史观。一提到革命必定是烽烟滚滚血横流,慈禧必定是反动保守的,李鸿章必定是“卖国贼”,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遗憾的是,这不是真实的历史。
我们大多数人对历史人物的判断,都简单而粗暴,只是君子与小人、仁君与昏帝、好人与坏人的二为分法,没有灰色地带。遗憾的是,人性是複杂的,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黑与白之分,每一位历史人物的选择都没有对错,他们只是基于当时的内外因素做出了合理的抉择,与其区分好与坏,不如从利与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历史,有些问题自然不难理解了。历史格局的演化自有其规律在,所有的局中人都是迫不得已,慈禧如此,李鸿章如此,末代摄政王载沣亦是如此。钱穆先生曾说,对历史应报以温情与敬意,读历史亦是如此。很多时候,历史是没有真相的,或者说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相,却永远无法企及。我读历史,更多的关注其背后的逻辑,以及由此获得的感触。
晚清之际,风云激荡,中西文明以血与火的形式火碰撞与交流,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类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寻求救世良方。眼看大厦将倾,企图孤木撑天,迷茫与希望,改良与革命……
客观地说,晚清的覆亡,从甲午战败后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此前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只能算得上是阵痛,并没有触及帝国的命脉。甲午一战,泱泱大国竟然败给了蕞尔小国,这是时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从帝国重臣到士绅阶层再到普通百姓,心头普遍瀰漫着一股屈辱与悲愤的情绪。从此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脉络:清廷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
晚清新政在清末历史上是一抹难得的亮色,但清廷在这场系统性的改革中逐渐失去了控制力,权力与权威受到了质疑和损害, 由改革所引发财政问题更是成为清廷的一个死结。在此过程中,清廷也丧失了支撑传统帝制王朝的利益集团基础,即士、军、绅。而传统士、军、绅恰恰又不足以支撑一个宪政国家,故民初宪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晚清最后十年改革,以地方自治为旗帜,其结果,是将维繫传统地方秩序的“绅”,纳入一种新的“地方咨议局”系统内。“绅”对“咨议局”怀抱极大的希望,并非因为他们认同其宪政特质,而在于“咨议局”是变革时代维繫他们既有社会地位的要津。清廷一再在国会问题上拖延、推诿,与“绅”希望儘快确立起新社会地位的愿望背道而驰,反倒给了革命党渗透崛起壮大的机会。儘管晚清的最后几年,各种现代化举措正在迅速推进,但帝国的柱石却已被掏空,民心已失,覆亡已是其必然的归途。
1911年武昌起义后,旅居日本的梁啓超写下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来之中国,若支破屋于淖泽之上,非大乱后不能大治,此五尺之童所能知也。武汉事起,举国云集回响,此实应于时势之要求,冥契乎全国民心理之所同然。是故声气所感,不期而治乎中外也。今者破坏之功,已逾半矣。自今以往,时势所要求者,乃在新中国建设之大业。而斯业之艰巨,乃什百于畴曩,此非一二人之智力所能取决,实全国人所当殚精竭虑以求止于至善者也。
儘管清政府的自救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终结了晚清,但梁啓超所言的新中国建设问题并没有因此被打断,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本身就是新中国建设中的一部分。
我试图用自己的文字沖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和金粉,力求在原始的档案历史材料之上,还原事实真相,以晚清历史大事件为线索,探索帝国崛起被打断的原因。
写作本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到我上大学就开始动笔,断断续续直至毕业多年才得以完稿,其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我终身坚守的誓言。作为一个新人,也许其中还有很多不足,部分观点也有待商榷,但我确实是尽力了。
以此为记。
2016年5月14日,写于西北一座雨水中荒凉的小城
文摘
1793年,中国农曆癸丑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
这一年的西方很热闹,法国那位“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在军鼓和“国民万岁”的呼声中被推上了断头台,二十四岁的拿破仑刚刚抵达土伦港前线,乔治?华盛顿正在美国激情澎湃地演讲着只有135个词的史上最短的总统就职演说。遥远的英国,一支从英吉利海峡出发的由七百多人组成的使团分乘军舰“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正行驶在茫茫海面上。
地球的另一端,大清帝国却显得十分宁静,没有天灾,没有战乱,天上没有星星闪烁,地上也没有到处冒红光。清朝的子民们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沉浸在闭关自守带来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中。皇帝和多数大臣不料界外部的世界和时代的变化,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八大胡同夜夜笙歌,大烟馆内云雾缭绕,仿佛外面的世界发生的那一切都与他们毫无关联。
17世纪以后,科技革命席捲了整个欧洲,自然而然地又带动了工业革命向世界範围内的扩展,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使织布工人的效率提高了一倍;1764年,兰开夏郡内的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大大加快了织布的速度,也刺激了对棉纱的需求;1769年,瓦特製成第一台蒸汽机,从此人类的发展进入了狂飙突进的全新时代;1807年,美国人富尔敦製造了第一艘汽船;1814年,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
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的经济,让英国从孤悬海外的岛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中期,经过康雍乾三朝,封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取得较大发展。乾隆末年,中国的农作物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人口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手工业与商品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景德镇的瓷器达到历史高峰,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这一切都在表明,一个崭新的盛世已经到来。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西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气候严酷,物产瘠薄,人烟稀少,再加之宗教气氛浓厚,经常处于分裂状态,难以产生强大的政治势力威胁中央王朝的政权;西北仅有一线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沟通;北部是内蒙古高原,东北部是白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这也不难理解,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规模较大的文明都需要依赖农业为主的生产力。
清王朝始终抱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自认为华夏就是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来处理与外部的一切关係。这种地理中心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地理观念,也是一种文化中心观念。千年以来,全体中国人对“天朝上国”的自信已是无可动摇,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随着君主专制逐渐强化,统治者闭目塞听,再加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国内统治者以及广大百姓对外界几乎没有了解,还处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不能自拔。
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古国。然而两者之间却极少有过交流,正如华裔历史学家徐中约所说:“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同,两者没有碰撞”。
历史的车轮吭哧吭哧进入18世纪之后,开始了加速行驶,英国这列火车借着工业革命的春风高速行进在宽敞大道上,而中国这辆破旧的马车却已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古老中国与西方国家终于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个人就是马戛尔尼此时的他,正站在“狮子号”上的甲板,眺望着远方的碧海蓝天,尽情地呼吸着东方的气息,内心複杂而激动。他的目标在遥远的中国——那是欧洲人一心嚮往的圣地。
乔治?马戛尔尼,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官,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表兄。在接受这次中国行的任务之前,他曾经做过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在出使俄国进行贸易谈判时,马戛尔尼充分发挥三寸不烂之舌的特长,为在俄国经商的英国商人争取到了公平的权益,让英国政府对他刮目相看。此次访华,英国政府派出了这位老牌政治家,期望他能代表伟大的日不落帝国向东方皇帝问好,名义是给乾隆皇帝祝寿。
事实上,所谓的祝寿只是一个幌子。马戛尔尼的此次访华,是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派遣,带着重大使命来求见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
18世纪末的英国,在经过将近一百年的积累和努力后,将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远远抛在了后头,正在大踏步地迈向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日益强大的工业文明正在大西洋上冉冉升起。儘管英国国土有限,人口不多,却由于商品经济、机械化及工业革命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作为工业革命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英国人感到十分自豪。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它到外部世界去开拓市场,开拓原料产地。由于中国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铅、锡、铜、毛呢棉花等“洋货”在中国本土销路不畅,而中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在海外市场大受欢迎。在中国瓷器流入欧洲之前,欧洲人的餐桌上大多摆放的是铁质和木製餐具,富裕家庭和上流社会则会使用金银器具。在见识到中国精美的瓷器后,他们被彻底震撼了!
沃肯曾指出,“在西欧见识到中国瓷器以后,中国瓷器就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是一种不是本地陶器所能比拟的器皿,中国瓷器所特备的优点,它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都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
在当时的大清帝国,外国商人的贸易被长期限制在广州,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扭转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打开中国的国际贸易大门,在征服了印度之后,英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所以,马戛尔尼此次来中国,其实是为了解决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均衡问题,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係并开展扩大经济贸易往来。
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狂热追寻和嚮往缘于那本风靡欧洲的超级畅销书《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当时的欧洲颳起了一阵最炫“中国风”。在书中,马可?波罗告诉自己的欧洲同乡,“中国地大物博,国泰民安,臣民身居大厦,衣着锦绣,地面生长着奇花异草和丁香、八角、肉桂、豆蔻等西方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高级调味品,地下则遍布黄金白银等西方人梦寐以求的物品。”
这本书忽悠了不少渴望黄金和香料的西方冒险家,其中之一就是哥伦布。也由于这篇游记,使得欧洲的探险家们前仆后继,寻找通往遍地黄金的大汗乐土之路。
张宏杰在他的《饥饿的盛世》中这样写道:“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从制度到道德,都比欧洲优越。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事实上,我们的主人公马戛尔尼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迷。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这一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他走过了大半个世界,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却唯独没有来过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他曾写诗吐露内心憧憬,表达对遥远中国的嚮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
为了表示对遥远的东方古国的崇敬,敲开中国这扇财富的大门,英国皇帝对于使团的规模和人数也是精心考虑,为使团的组成进行了周密的準备。
这是一个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具有商务和政治的双重目的,使团人才济济,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有科学家、园艺家、作家、翻译家、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僕役等,还有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大量军事人员,算上水手将近700人,其中还包括马戛尔尼的挚友,也是使团副使的斯当东和年仅12岁的小斯当东。
记住这个红头髮蓝眼睛的小男孩,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名字将会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读者评价
本书作者与我相识已久,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90后才子。他低调而勤奋,在90后中出类拔萃,年纪轻轻便能对历史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殊为不易。
——云石,着名自媒体人
晚清时代连线着两头,一头是中国传统官僚社会,一头是中国被迫进行的近代化的转型历程。在这个人心浮躁的年代,作者年纪轻轻却能沉下心,抛开历史教科书的陈腐论述,力求破除单一的非黑即白的叙事逻辑,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历史观点,堪称90后着史者之楷模。
——李金海,《贺兰山》作者